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
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
【哲学论文】导语,您所阅览的本篇共有131798文字,由袁文淳仔细纠正后,上传到美文档!意义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yì yì,一指人或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二指内容,三指美名、声誉;四指作用;五指价值。事物存在的原因、作用及其价值。出自《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义也。”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假若你对这文章感觉哪里不好,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
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一篇
摘 要:本文介绍和评论了莱伊、以及作者本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批判学派”——20世纪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先驱,其代表人物是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的研究概况和主要见解,以期引起学术同行的关注和深入探究。
关键词:莱伊 批判学派 学术研究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nd discusses researches and views on the critical school of thought as a whole by abel rey, v. i. lenin, and li xingmin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school of thought are e. mach, h. poincaré, p. duhem, w. ostwald, k. pearson.they are pioneers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in 20th century.
key words: a. rey, v. i. lenin, the critical school of thought, academic research
批判学派是活跃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学派以及哲学学派。历史已经表明,该学派是现代科学革命(物理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2]的先驱,在科学史、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WWW.meiword.cOm
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3],他们既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即是名副其实的哲人科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虽然肇始于对世纪之交的科学危机的反应,但是,由于他们深厚的哲学素养以及对科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机敏反思和洞见,他们在哲学上也颇有建树。要知道,他们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伟大哲学传统的继承者,是“前现代”科学哲学的创造者和集大成者,是逻辑经验论及其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嚆矢和滥觞,也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线和酵素。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皮尔逊、马赫、彭加勒在20世纪初对的纽带;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承载者和缔造者。
1991年伊始发表的论文[14]是一篇关于批判学派的综合性研究论文。我在该文中论述了三个问题:(1)批判学派的根本特征。批判学派否认物理学可以划归为经典力学,对经典力学和力学自然观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批判(并且对物理学革命也作出了诸多建设性的贡献)。这是批判学派的根本特征,也是它的标识和判据。(2)批判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共性是:对物理学发展形势有比较清醒的看法,并致力于科学的统一;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历史批判的研究方法与写作风格;普遍赞同思维经济原理;充分肯定科学美在科学中的巨大作用;第一流的科学家,名副其实的思想家和众多领域的“漫游者”。(3)批判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在科学思想和自然观、科学观、基本的哲学立场、社会观点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这篇论文的观点在《马赫》一书中的第九章“马赫与批判学派”得到拓展和深化,其中新涉及到马赫与其他四位代表人物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形而上学的不同态度。
批判学派的一个显著的共同思想特征是,其代表人物都是进化认识论的先驱。1994年初,我就揭示了马赫的进化认识论和自然主义思想[15]:世界或自然界是一个自然的、统一的整体;思想适应事实和思想彼此适应是生物反应现象;科学是一种生物的、有机的现象;人生不是一块“白板”,而具有天生的倾向和“观念”,它们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所有的知识和理论都是可错的、暂定的、不完备的,其形成具有偶然性。1995年9月28-30日,我赴香港科技大学参加“中国逻辑与当代语言哲学”研讨会,为会议提交了关于科学中的语言翻译的论文[16]。该文论述了批判学派的先声和库恩的“回应”。我在最后的评论中表明:1)马赫对语言在科学中的价值的重视,彭加勒关于科学是未加工事实的译文以及翻译的可能性在于真关系的不变性的思想,迪昂关于科学的结构和科学基本操作中的语言翻译的论述,都对20世纪的语言哲学有所影响。尤其是迪昂的理论整体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爱因斯坦、纽拉特、卡尔纳普、蒯因等人的意义整体论思想。2)彭加勒和迪昂关于科学中的语言翻译的论述基本上停留在同一理论的范围之内,尽管迪昂也涉及到同时代的不同理论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库恩的着眼点则在于后者,尤其是历史上相继的理论的翻译问题。他从语言翻译的观点把不可通约性论题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彭加勒没有提及或没有意识到科学中语言翻译和诠释的区别。迪昂已明确涉及到这个问题,并就同一理论中的诠释和不同理论之间的诠释作了剖析。库恩的贡献在于,他对翻译和诠释作了明确的区分,并探讨了二者的特征。4)迪昂已提出测量方法是使翻译变为可能的词典的命题,这实际上已意识到测量或词典是联系主体(科学家)和客体(客观实在)的中介。库恩对“词典”的论述颇有见地:无论是它的形成、结构、变化,还是它一面向着世界,一面向着心智,都给人以启示。
20xx年,我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其他四位代表人物,从而论证了批判学派是进化认识论的先驱[17]。彭加勒的进化认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几何学和时空理论上。在这里,他既不满意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也反对传统的经验论观点。他用先于个人经验的“祖传的经验”诠释人的几何学和时空概念的起源,认为这是人类在漫长的生存斗争中,在对外部环境的不断适应的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逐渐形成的。在科学观和客观性概念上,也渗透着他的进化认识论思想。在彭加勒看来,科学定律只不过是近似的、概然的、暂时的而已,科学理论是暂定的和易崩溃的。他虽然认为科学发展中有危机和革命,但总的看来还是以进化的形式进步。他把客观性理解为主体间性,也隐约地透露出人的心智结构与自然的结构同构的思想。迪昂的进化认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科学观上:科学发展是渐进的进化,物理学定律是暂定的和相对的,完备的理论是自然进化的理论即自然地趋近自然分类的理论。奥斯特瓦尔德的进化认识论思想表现如下:科学推理的普遍形式即因果律只不过是人类在适应外界环境的长期进化过程中的经验的积淀,就个人而言它无疑先于他的经验,但就起种族而言则是后验的;科学是自然的事物,是人为人的目的而创造的,具有不可消灭的不完美的质;形式科学表面看来似乎是心智的天生的质或先验判断,但它们实际上像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一样,也是实验的和经验的;知识或科学兼有主观特征和客观特征。皮尔逊认为,意识、理性等等都是生命进化的结果;宇宙的同一在于思维肉体工具的同一,心与物是同构的;思维关系和事实关系一致,物理过程和理性过程等价,物理宇宙和心理宇宙终极要素相似;思维经济、科学定律和时空概念的起源都与生存斗争有关。
早在1986年,我就注意到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哲学思想的张力特征[18]。在两年后出版的小册子中[19],我径直把彭加勒作为案例,揭示了他的哲学思想的两极张力特征。在《马赫》和《皮尔逊》中,我在论及二人的哲学思想时,也指出了其张力特征。尤其是在《迪昂》中,我专用一章论述迪昂的“班驳陆离的张力哲学”。迪昂的多元张力哲学的灵感之源是亚里士多德、帕斯卡、托马斯•阿奎那,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多恻面形象也迫使他在构造概念世界时不能过分地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或墨守于某一个思想流派。迪昂不仅与其前驱保持了思想张力,而且与批判学派的其他成员之间保持了思想张力。迪昂的张力哲学也表现在他善于在各种对立的“主义”和形形的对立的观点和思维方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他甚至在科学、哲学和宗教之间也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对批判学派甚或哲人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多元张力特征的详尽研究,则是我刚刚发表的长篇论文[20]。马赫的主导哲学思想是感觉经验论或要素一元论,它虽然在某些方面显得彻底和激进,但是并不狭隘和极端,其内和其外都充满了鲜活的张力。首先,它包容了经验论的多个变种的成分,诸如实证论、现象论、操作论、工具论、描述论、呈现论(presentationali或presentationi)、实用主义。这些成分不仅相互交融和制约,而且马赫对每一成分或多或少有独特的理解和必要的限定。更重要的是,马赫哲学思想中包含着诸多非经验论的乃至反经验论的成分,尤其是其中的理性论、约定论、反归纳主义更引人注目。彭加勒的哲学创造和主导哲学思想是约定论,它内容丰瞻,其八大内涵中溶入了(关系)实在论、(科学)理性论、(温和)经验论的要素。他通过限定约定的辖域,排除极端理性论(先验论)和狭隘经验论(感觉论和实证论),在各哲学要素之间保持了张力平衡。迪昂的哲学创造和思想特色是理论整体论,其八大内涵本身就包含诸多哲学体系的合理因素,是一个多元张力综合体。它的哲学思想可用本体论背景上的秩序实在论、方文脉内的科学工具论和认识论透视下的理论整体论来涵盖,这三种类型的异质哲学之前的定语指出其大致范围,加上对它们的种种诠释和限制,从而保证它们会聚于迪昂的思想,虽有张力但不致发出剧烈的冲突。皮尔逊的哲学是以怀疑和批判为先导和特征的,以观念论(唯心主义)自我标榜的,带有明显的现象论、工具论和实证论色彩的,属于经验论范畴的感觉论的认识论,即观念论的感觉经验论,这种哲学本身就蕴涵着某些张力。此外,他在对一些具体的问题的看法上也是有张力特征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哲学是能量论(唯能论)或能量一元论。该哲学认为能量比物质更根本,是宇宙的真正基元,因此也可称其为能量实在论,从而在物质论和观念论之间保持了张力。除此而外,他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方法也具有某些张力特征。批判学派之所以在哲学上采取多元张力的立场,其原由在于:他们深知自然、人、人的活动和文化都具有两极张力或多极张力的特征;他们对哲学遗产以及科学和哲学的本性有清醒的认识;问题的驱使;外部条件的约束。通过比较批判学派的各个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不难看出,该学派在哲学上并非铁板一块,其成员的主导哲学思想有很多差异,他们的同点也不是什么观念论;以科学立场和态度作为划分批判学派和力学学派(机械学派)的标准,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莱伊把马赫等人称为“唯能论或概念论学派”是有问题的。“概念论学派”的称谓并不确切,“唯能论学派”的称谓与历史事实不符。其理由在于,在我所谓的批判学派中,只有奥斯特瓦尔德才是真正的“唯能论”者:奥斯特瓦尔德是能量学(energetics)和能量论或唯能论(energeti,energi)的创造者和集大成者;迪昂的科学生命的核心是能量学或广义热力学,他力图把一切物理现象都还原为热力学,但对作为哲学学说的能量论似无热情。马赫不赞成能量论,这一点连奥斯特瓦尔德也了如指掌。彭加勒既避免把他与能量学联系起来,也避免把他与机械论物理学联系起来,他不支持唯能论。皮尔逊对能量学和唯能论也未表现出什么兴趣。我在1988年初对此已很清楚[21]。
批判学派的哲学中也包含着许多后现代的思想要素(对主体性的张扬,对实在论、客观性和合理性的冲淡,对经验论原则的削弱,一些超越时代的科学主义睿智等等;以及诸多有名的命题,诸如不充分决定论,观察渗透理论,判决实验不可能,归纳法不切实际,科学发明是选择,直觉是发明之具,关系比实体更根本,科学中充满翻译和诠释等等),我在已发表的诸多论著中零散地有所涉及。我准备有机会就“批判学派的后现代意向”写篇论文,对此进行比较集中、比较深刻的论述。
[参考文献]
[1]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卷(1981), 第6期,第30-38页。该论文的全部或部分浓缩后来进入拙作[10]和[11]之中。最近偶然发现,在一本多位人士合写的著作中,某某名牌大学某某教授的有关观点和文字与我的论文和文章中的观点和文字惊人的相同或相似,我只好惊叹“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奇迹”出现了!
[2]李醒民:“马赫:维也纳学派的先师和逻辑经验论的始祖”, 《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6卷(1994),第5期,第1-10页。或参见文献[3]的有关章节。
[3]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我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专著:《彭加勒》(1994)、《马赫》(1995)、《迪昂》(1996)、《皮尔逊》(1998),以及李醒民:《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2年第1版;李醒民:《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1994年 第1版,1996年第2次印刷;业强出版社(台北),1996年第1版;李醒民:《伟大心智的漫游——哲人科学家马赫》,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1995年第1版。
[4]可参见《皮尔逊》第七章。或者参见李醒民:“科玄论战中的皮尔逊”,《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1卷(1999年),第1期,第49-56页;李醒民:“皮尔逊思想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5卷(1999年),第3期,第42-47页。
[5]a. rey, la théorie de la physique chez les physieiens contemporains,paris,1907.以下引文均转引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266-269、276-278页。
[6]a. rey, la philosophie moderne, paris, 1908.以下引文均引自:《哲学笔记》,党校出版社(),林利等译校,1990年第1版,第601-604、609-615页。
[7]于1908年2-10月在日内瓦和伦敦撰写该书,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是文献[5]的中文版本,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8]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n,1861-1916)不是比利时人,而是法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他的译名应为“迪昂”,而非“杜恒”,这种误译和混乱不应再继续下去了!马赫也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
[9]李醒民:“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哲学卷(中)》,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1998年第1版,第1247-1285页。
[10]李醒民:《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出版社(成都),1983年第1版,1984年 第2版。该书在短短的数年内至少连印6次,发行量多达10余万册,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深广。
[11]《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38-339、566-568页。
[12]李醒民:“马赫、彭加勒哲学思想异同论”,《走向未来》(成都),第3卷(1988),第3期,第92-97页。
[13]李醒民:“论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求索》(长沙),1990年第5期(总第57期),第51-57页。《世界科学》(上海)以此文为基础,发表记者访谈录“哲人科学家研究问答——李醒民教授访谈录”,1993年第10期,第42-44页。
[14]李醒民:“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1年第1期(总第53期),第99-107页。
[15]李醒民:《马赫》,第139-159页。或者,李醒民:“马赫:进化认识论和自然主义的先驱”,《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7卷(1995),第6期,第1-9页。
[16] 李醒民:“论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大自然探索》(成都),第15卷(1996),第2 期,第100-106页。或者李醒民:“論科學中的語言翻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主編:《邏輯思想與語言哲學》,學生書局(臺北),1997年第1 版,第145-162頁。
[17]李醒民:“批判学派:进化认识论的先驱”,《哲学研究》(),20xx年第5期,第52-57页。(该文在作者撰写论文“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时尚未发表)
[18]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准则”,《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总第40期), 第143-156页。英文摘要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opposing extrems: a highly efletive principle of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ce 刊于第ⅷ届国际逻辑学、方和科学哲学会议论文摘要集,莫斯科, 1987年。
[19] 李醒民:《两极张力论.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西安),1988年第1版,第14-44页。
[20] 李醒民:“论哲人科学家哲学思想的多元张力特征”,《学术界》(合肥),20xx年1期,第171-184页。
[21] 李醒民:《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1994年 第1版,第86-132页。
先验语用学与基础论辩_其他哲学论文 第二篇
[摘要] 如今,德国的先验论传统与英美哲学传统的合流已成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阿佩尔(k.o.apel)的"先验语用学"正是这种融合的结晶。它把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哲学与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试图为科学论构筑一种合适的研究平台,同时也试图给出一种"终极有效的"奠基策略来规避相对主义。尽管"先验语用学"尚处于形成之中,其边界还有待于通过论战来作进一步的界定,但它的研究方向和追求目标无论如何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 先验论辩 语用学 科学哲学 奠基策略
迄今为止,我们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研究还尚未对德国哲学、尤其是先验哲学的演变动向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无疑是一种偏颇。其实,无论是r.bubner、erlangen学派的k.lorenze和j.mittelstrass,还是哈贝马斯和阿佩尔都在先验论的方向上大大地深化了科学哲学的研究。阿佩尔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试图把先验论从康德的意识论领域移植到语用学中来,从而对"科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重新作出回答。他指出:"在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巳经不是什么秘密了?quot;[1] 我们知道,科学哲学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如何为科学知识作出辩护的问题,而语用学对当代科学论的贡献不仅在于经验地呈现知识的生成过程,同时还试图为这种知识提供有效的辩护。问题是,什么样的辩护才算是有效的呢?是否存在一种"终极的"辩护呢?换种说法,语用学一般不相信"真理"之类的词,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总是基于特定的条件与地方性的情境进行研究的,那么凭什么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并且能够获得人们的认同呢?认同当然要经过现实的商谈与论辩过程才能达成,然而商谈与论辩又为何总是能达成认同呢?了解了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的解决方案和奠基策略,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Www.meiword.CoM
一
阿佩尔曾对自已的思想作过如下的概述:"我本人的先验语用学之路细想起来是这样的:最初首先接受了莫里斯(进一步说是皮尔士)所达到的三维指号学的'施行'(pragma)概念,通过将指号的解释者('发送者'与'接收者')进行主题化,从而在语言哲学层次上返回到古典先验哲学的主体问题的建构上去。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2]当然"先验语用学"不是上述理论的简单相加,而是"哲学的转换"。"转换"(transformation)意味着一种双向性的转换。一方面使经验的东西按先验的方式得以重构,通过奠基使语用学摆脱相对主义的困境;另一方面,同时也把康德的先验哲学按施行论的方式加以转换,转换到语用学的维度上来。这是两个互补的转换方向。"我的课题是,不仅阐明先验语用学对现代科学的经验的必然性,而且也阐明用先验语用学诸概念来批判地重建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的'先验哲学的必然性。([1],s.16)
莫利斯所引入的"语用学"(pragmatics)一词,原本是在与语型学(句法学)和语义学的维度相区分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是真正赋予它以哲学内涵的还是维特根斯坦?quot;语言游戏"说与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论。按照"语言游戏"说,语言的意义并非取决于它对事实的表达,而是取决于它的用法,即在"生活形式"的语境中的使用;按照言语行为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它不仅要表达某种经验事实,更主要的是还要"有所作为"。用奥斯汀的话来说,"说话就是做事"。从两者的结合中可以看到,语用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哲学的方向,即从对语言本身的转向对制约语言使用的情境条件的构造。构造的要件不仅涉及谁说话,谁接受,还涉及说话与接受的方式与媒介。当语用学把话语?quot;主体"作为"共同体"来构造时,也就意味着一开始就把"主体性"作为"主体间性"来理解了。
阿佩尔接受了上述语用学的基本主张,甚至把科学也直接理解为是"语言游戏"中的一种。他认为,只有从"语言游戏"所提供的主体间性出发,科学才能真正有效地摆脱"方唯我论"的缠绕。在语用学看来,任何人都没有独自拥有真理的特权,任何一种主张都己经包含了有效性的要求,它要想表明自己的科学性,首先必须能让别人接受,得到他人的认可。因此仅仅给出一种证明或者经验事实的证实是不够的,而必须付诸于主体间的谈论(diskurs)与论辩(argument)。只有通过论辩,我们才能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辩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佩尔用"论辩共同体"来取代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用学返回到了希腊的论辩传统上来了,从而一改以往的知识论只注重亚里士多德的"篇",而轻视其"topika"(论辩篇)和"修辞学"的偏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尽管论辩术不具有严格的三段论法所具有的普遍的强制力,然而人们在事实上想达成相互的认可,还是有赖于论辩中的说服。他觉得,论辩术所特有的关于事实的归纳法似乎特别适宜于这类说服的任务。[3] 但是历史上(包括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内)的知识论始终不宵于论辩术,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论辩自身的局限:首先,论辩不具有普遍有效的说服力,它的有效范围只限于在场的论辩对手。其次,用于支持论点的根据也只局限于有限的经验事实的归纳,而不足以支持带普遍性的命题。最后,它很容易演变成类似于智者们的诡辩术。到了近代,由于培根对归纳法的大力倡导,使长期以来遭人遗弃的论辩方法又重返科学的殿堂。这使得证明与论辩这两种科学的论证策略的地位有可能被重新颠倒过来。一方面论辩术中用于寻找例证的方法(归纳法)有望使科学知识建立在可靠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相反,证明方法的使用范围受到制限,其有效性也大打折扣,并最终沦为语言学中的修辞工具。
如今人们之所以重新估价论辩术与修辞学,个中的原因还与科学观念的转换不无关系。库恩曾把十八世纪以后的科学称作"培根的科学"。一方面,与十七世纪那种以数学与理论为优位的表象主义的科学观念不同,新的知识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是在改造对象的实验活动中构建的,并且在与产业的联系中检验自己的有效性和力量。另一方面,科学已成为一项公共的事业,而不是科学家个人的"独白"。于是库恩才强调,科学家只有通过劝导与说服来动员他人的参与,才能把自己想法变成一项普遍接受的事业。如此说来,科学家不再是真理的代言人,要想为自己的研究作出辩护,他们还需重新找回被遗弃二千多年的论辩方法。当然,这不是要人们都去重新师从有头脑、能言善辩的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而是要求在逻辑证明的手段之外重新寻求理论的根据,以及持据而辩的策略。
但是简单地回复到古代希腊人的论辩策略还不足以为科学奠基。道理不难理解,谁能担保论辩总能达成共识?即便达到了共识,又如何保证它没有受到系统扭曲的污染,以及权力因素的干扰?要想解决这些难题,还须对可理解的条件进行重构,因为只有经过合理性重构的"论辩共同体"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奠基的功能。为此,阿佩尔根据"论辩共同体"在科学活动中的不同作用,将它区为三种类型:即"现实的交往共同体"、"先验主体"和"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当然这不意味着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而是指同一种"论辩共同体"的三种不同的位格。
关于"现实的交往共同体",阿佩尔的理解与哈贝马斯大同小异。无论维特根斯坦、库恩、还是费耶尔阿本德都执著于描述历史和现实的情境与制约条件,因此最终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地方性的情境条件加以重构,看看什么是普遍交往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用这样一些理想性的条件来构建成新的研究主体,这时我们就已经进入"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中了。按照哈贝马斯的"反事实的"在先性原则,正是因为现实中存在种种交往的障碍,我们才预设某种不含强制和扭曲的交往条件。因为当你知道什么样的状况是"被扭曲"时,你肯定已经清楚什么是未被扭曲的状况。[4] 按阿佩尔的理解,理想状况的在先性意味着某种先天的条件"总是已经"(immer schon)被设定,并且在起制约作用了。
关于"先验主体",阿佩尔有自己的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我们在玩游戏的同时一边修正着它的规则。商谈(diskurs)活动也具有同样的反思的功能。我们不仅能就某事进行商谈,一当商谈出现问题时还能就商谈本身进行商谈。就商谈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所进行的商谈就叫论辩(argument)或叫"元商谈"。哈贝马斯的看法是,"元商谈"也是一种经验性的活动。然而在阿佩尔看来,当我们通过反思达到了"元商谈"时,便已经赋予了这种论辩以先验的位格,再也不能与经验性的论辩活动混为一谈。人们不可能被封闭在被给定的"语言游戏"中,他们总是能够超越并达到新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普遍的交往共同体,也是一切经验理解的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按康德对先验性的理解,作为一切经验可能性的条件的东西,其自身不可能是经验研究的对象。在区分哈贝马斯的"理想交往共同体"与阿佩尔的"先验主体"的准则上,科林斯把握得十分准确。他指出:"在我看来,在哲学传统之外认可非经验的理论方向的,是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而在处理有效性基准和前提的,是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或者说这是一种奠基哲学,是一种追溯回到作为终极奠基法庭的,先验地施行(pragma)的论辩或论辩共同体的先验哲学。"[5]
现在我清楚这样一点,当现实的论辩(共同体)在合法性上出现问题时,便要求以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为主题进行论辩,于是论辩活动便具同时有了"先验论辩"的意义。在阿佩尔看来,这种"先验主体"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可还原性,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是一切经验可能性的"终极的"条件了。对之,只要不出现自我矛盾,就不可能加以否定。在这里,先验性的特征表现为反思性所确定的先验前提不是外在地设置在实在的交往共同体之上的,而是"总是已经"包含在现实的共同体中的有效性要求。我们之所以不可能否定它,那是因为,即便否定了,现实的论辩共同体仍然会重新提这种有效性要求。这便是"终极奠基"的奥秘所在。
二
阿佩尔认为,语用学与先验哲学的融合趋势其实已经包含在从奥斯汀的"语用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s)到哈贝马斯有关言语行为的"双重结构"理论发展之中了。在这些理论发现之前,人类语言始终为逻各斯优位的思想所占据。语言的功能被限定在"命题"和"表达",而言语中"施行"层次的问题恰恰被划归到行为主义的经验课题中。哈贝马斯的"双重结构"原理使传统的语言观与知识论呈现出了新的生机。比如,何谓"真"?在塔尔斯那里,这是一个不同于对象语言的元语言的陈述。而在语用学看来,"真"是一种对人类知识作出反思而形成的陈述。这种反思无疑是通过共同体成员对真理性的要求来实现的。借助于言语行为中的施行成分(performativa),我们就有可能把交往行为对真理性的要求以命题形式表述出来,使之进入科学知识的范围。可见,科学知识是"命题内容"与"语用力量"的并存,或者说是"knowing that"与"knowing how"的并存,在阿佩尔看来更是关于对象之知和关于对其自身的反思之知的并存。离开后一种知识,人类的逻各斯就会丧失自我奠基、自身辩护的能力。因此如果让语用学仅仅停留在莫里斯和卡尔纳普那样的经验语用学上,恐怕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既然如此,超越经验语用学中的描述主义而转向"先验语用学",也正是语用学对自身所提出的有效性要求。([2],ss.18-19)
转向"先验语用学"的必然性也可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中找到旁证?quot;批判的理性主义"的意图原本是为了拒斥科学论中的怀疑论观点,为此,科学共同体对真理性的要求本来只有以论辩行为为前提才是可能的。可是波普本人却热衷于逻辑主义的论证程序,而遗忘了先验的施行因素。这无疑是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问题就出在波普不理解论辩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思功能。科学无疑需要"普遍的规则",而规则只有得到科学家共同体普遍认可才有效,因此只有付诸于论辩才能达到。论辩是一种辩护行为,包含了劝说、说服。不过辩护性的说服不仅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结论,在接受结论的同时也要连带接受达成结论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波普对论辩的忽视,致使它成为费耶尔阿本德手中的有力武器。
可是在费耶尔阿本德那里,论辩不是被看成是奠基的方式,而是被当作消解任何基础的手段。按竞争理论的"增生"(proliferation)原则,任何魔术,神话、故事都可以和科学一样,通过论辩的劝说而让对方相信。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为"普遍性规则"的奠基而操心。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罗蒂那里。罗蒂用"连带性"(solidarity)来取代"客观性"及其奠基要求。在阿佩尔看来,费耶尔阿本德和罗蒂都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上去了。他们的问题就出在忽视了科学共同体的论辩所具有的"先验反思"的功能。这样一来就丧失了理论比较的客观基准,致使科学沦落到与巫术、神话和故事同等的位置上去了。从上述两种倾向的谬误中,阿佩尔有理由得出结论,只有先验语用学才能有效地揭示论辩的反思与奠基功能,才能在经验科学与先验哲学之间寻找到沟通的桥梁。无论何种经验科学,在其形成理论的过程中,先验的论辩都是一个无可规避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科学论要么导致自以为是的科学主义,要么滑向类似于费耶尔阿本德的反科学主义立场上去。 ([2],ss.19-20)
站在"先验反思"和"先验位置"的层面上看,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也是成问题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三个世界",而在于划分"三个世界"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标准。比如人们对话语和理论所提出的有效性要求,按波普的划分法它们应属于第二世界,可是这些要求却又与经验的和心理学意义的行为无关。就这些要求的内容而言更应该划归于第三世界。波普的麻烦首先是,有效性要求、论辩、及其反思所依据的一般性前提,这一切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既可以同时属于三个世界,但挚梢圆皇粲谄渲腥魏我桓觥f浯危杂诓ㄆ昭傻?quot;无主体的认识论"来说,尽管它可以这样那样地划分不同的世界,却无法在"先验位置"上反思不同世界之间的关系。因为原则上三个世界的划分者一次只能置身于其中的一个世界。要是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客观地划分出不同的世界,除非设定一?quot;先验主体"来进行反思性地考察。可是波普一开始就犯了"抽象的谬误",不仅抽离掉了能够进行商谈的实在主体,同时也抽离掉了能够进行反思的"先验主体"。阿佩尔说,"在我看来,站在'先验主体'的角度看,这种关系(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能够被思考的,实在主体对规范的理解和遵守(或不遵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也能被思考。在此,我们并非回到康德以前的有关世界的形而上学实体化的柏拉图主义,同时也能与维特根斯坦和奎因之后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划清界线。"([2],s.21)
就拿现实中的论辩来说,它既可以是一种奠基的方式,也可以是一种策略行为,一种好强争胜的手段。作为策略性的论辩,其中不乏欺瞒、暗示、诱导……。它无需提出真理性的要求,只要能打动别人,说服对方即可,那怕强词夺理也无妨。正象费耶尔阿本德所说的那样,关键是面对论敌如何为自己辩护,以及论辩策略所取得的当下效果,至于自己所辩护的东西究竟是科学的知识,还是神话、巫术和故事都无关紧要。但问题是,我们的论辩难道是无前提的吗?要不然任何一种漫无边际的漫谈也叫论辩了。因此论辩本身必须同时是一种奠基行为,而奠基的本意就是持据而辩。一种基于根据的辩护,本身就意味着有先决条件了。任何一个科学家在其公布自己的成果时,就已经包含了为其论断辩护的方式及其条件,这表明他已经对自己的理论提出了有效性要求,即要求得到同行的普遍认可。对此,哈贝马斯已经?quot;理的交往共同体"原理中有过详尽的论证。但是阿佩尔认为,仅凭这样的原理还不足以对交往的条件进行有效的反思。要想解释经验,就必须超越经验的辩护方式,达到某种"先验的"或者说是"终极的"根据。三
波普和阿尔伯特曾借助于弗里斯的"三难推理"来对"终极奠基"的目标提出非难。按"三难推理",任何"终极的"的基础论证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论证如果不求助于某种独断的前提的话,要么只能求助于循环论证,要么势必陷入到无穷倒退之中。这时无论你怎么做,都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针对这样一种指责,阿佩尔争辩道,首先,"三难推理"无疑具有逻辑的辩驳力,但它只是对"无主体的认识论"而言的,或者只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境中才有效。其次,既便是一个基于合理化系统的演绎过程,也不足以否认其他形式的终极的基础论证。比如波普把逻辑先行设定为是一切基础论的前提,并且认定该前提是不能为逻辑之外的实践的前提所取代的。这难道不正是在先验反思的意义上探究的一种终极基础吗?波普对"终极奠基"的成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囿于句法-语义的维度而造成的。如果回到语用学的界面上来,"三难推理"便不足以成立。[6]
阿佩尔认为,正是由于波普学派对终极基础论证的取缔,导致了两个连他们自己都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是,当他们用具有普遍性的批判要求来替代"终极的"基础论辩时,势必会面临一个有关批判的可能性与有效性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基础论辩问题。可见,既便对逻辑主义而言,基础论辩也是时时面临,并且无可回避的。二是,如果放弃"终极的"基础论辩,那么波普所提倡的"开放社会"的理想将会丧失其合理性的根据。因为一经中止对该根据的讨论,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诉诸于信仰和非理性抉择,但蒙味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又与他本人的批判精神格格不入。([2],ss.21-22)
接下去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策略来进行基础论辩呢?在这一问题上,阿佩尔赞同斯特劳逊的"先验论辩"方案。斯特劳逊曾尝试对康德"先验演绎"中的辩护结构作出调整。调整后的论证是:当我们能把意识的条件归诸于他人时,才能把意识的条件归属于自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开始就进入到主体间关系,从而挫败对他人心的怀疑论态度。因为为了怀疑他人心的存在,怀疑者就必须使用他人心的概念。要是没有这个概念,他不可能有效地把自己的意识条件与他人的意识条件区分开来。事实上我们都在有意义地谈论"我的经验",这表明我们已经把自己和他人的意识条件区分开来了,同时也表明我们已经认可了作为区分标准的概念图式。有了这个标准,我们也就具备了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行为的条件归诸于他人的合法性根据。对于这种根据是不能轻易进行怀疑的,因为任何怀疑的成立也须得到他人娜峡桑捅匦胗行у乇泶镎庵只骋桑行у谋泶镉智∏〗⒃谒骋傻母葜稀u馐保骋烧呔拖萑肓私胛鹊霓限尉车兀此挥懈葑鞒龌骋桑此豢赡苡行у乇泶镒约旱幕骋伞7]
r.bubner把"先验论辩"的辩护策略归结为"别无选择性"(alternativenlosigkeit)原则是有道理的。[8] 由于对该原则所确立的辩护程序你既不可能再作回溯,也不可能有任何疑义,因此也可以说是"终极的"。阿佩尔所谓的"终极奠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我倒倾向于认为,论辩的间接的自相关性――它包含在关于一般论辩(的可能性条件)的先验语用学的谈论中――只有当它否定自身的真理性或不相信自身的真理性时,才陷于一种自相矛盾;这种情形发生在彻底的怀疑论那里,或者说发生在关于日常语言的话语――这种话语是关于话语之真理性的话语――的根本非一致性的谈论中。"([1],第313页)这里的表达既是对"别无选择性"原则的确认,又是该原则的运用。阿佩尔的意思是:我们一经确认了该原则,就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笛卡尔式的"阿基米德点"上来了。这是一个毋容置疑的出发点,任何试图对之提出挑战的人,实际上都是自挖墙脚。因为要使他的怀疑成为可理解的,"总是已经"预设了某种理想的制约条件,"总是已经"毫无例外地受制于这些条件了。
在阿佩尔看来,体现在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的"先验的语言游戏",无疑也已经预设了一个先验的论辩共同体的存在。只不过维氏没作这样的反思性区分罢了。在他那里,共同体成员之间对制约游戏的前提条件所作的谈论,本身也属于语言游戏。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关键是要让游戏玩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能量。对阿佩尔来说,一个具有先验的反思意识的人,不仅仅是一个游戏的参与者,同时也能自觉地意识到,并承担起对游戏的责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象波普那样一笔勾销基础论辩意义,因为这最终会把基础问题付诸于直觉。阿佩尔认为,任何诉诸于直觉的讨论,其实都将中止讨论本身的进行。所以说,只要讨论在继续进行(其实不可能停止),那么讨论?quot;终极奠基"和终极辩护的要求就一刻也不会停止。即便你人为地否定它,讨论本身也会重新提出这样的要求。结果正如阿佩尔所说的那样?quot;如果我们愿意用思辩神学的概念来表达,那么我们可以说,魔鬼只有通过自我毁灭的行为,才能够摆脱上帝。"([1],第318-319页)
先验的论辩共同体是"先验语用学"出于"终极奠基"的要求而构造出来的"先验主体"。它可以存在于任何可能的人为对任何可能的"语言游戏"所作的辩护中。至少理论上我们必须认定"先验主体"的存在,不然会陷入到日常的事实论辩之中,无视人类中存在普遍可交往性的事实;或者即便事实上接受了这种"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但是由于其合法性不能得到最终的确认,也会沦一种为乌托邦的构想。要是这样的话,即便你认可了它,也不可能自觉地对它担负起责任。换句话说,奠基是为了落实责任。"终极的奠基"就意味着终极的责任。从先验语用学的观点看:人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和伦理责任感的存在者,他不可能对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视而不见。一个有意识逃避普遍责任的人,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自己作为人的资格。
四
阿佩尔的基础论辩在结论上可能过于严峻,激起了一些多元主义者,乃至相对主义者的愤概,同时也招致了基础主义阵营内部的非议。在他们看来,阿佩尔与其说是在进行哲学讨论,不如说是在构造一种理想的宗教共同体。能维系这个共同体存在的唯一力量就是对它的虔诚和对异端者的排除。至少,如此严厉的强制性(尽管是理论上,而非"教规的"),其后果无疑是与语用学所提创的自由主义观念格格不入的。科林斯指出,阿佩尔对论辩共同体的构造,几乎是世俗化的教会理论的翻版。这种教会理论的基础是奠立在"教会神学"(theo-logisch)之上的。按照这种理论,不是徒们构成了教会,相反是教会决定了徒。当阿佩尔把论辩共同体升格到终极的"先验位置"上时,它对个体的交往行为来说就具备了无条件的优先性。那些拒绝接受理想交往条件的人,等待他的只有一种命运,就如同教会对待拒绝接受教义的异端者那样被逐出教门(excommunicatus)。于是先验论辩的"别无选择性"原则也就演变成了"教会之外无拯救"(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的原则。([4], s.352)在当今的国际一体化进程中,这种强制性原则已经暴露出了自身的种种矛盾与弊端。
科林斯的批评尽管尖刻,却也是中肯的。的确,论辩共迦绻豢季桶巡蝗贤淝疤岬娜硕季苤磐獾幕埃敲此裁匆猜壑げ涣恕k?quot;商谈"、"说服"云云都成为一句空话。另外,如果把阿佩尔的论辩共同体比作一个虚拟的"法庭"的话,那将是一个很奇怪?quot;法庭",这里没有控方,因此也没有辩方。"法庭"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表明理想法则的不可抗拒性。阿佩尔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不过这需要有个前提,即一开始就要求把一切可能的违法者和对法规的质疑者都排除在"法庭"之外。
与斯特劳逊相比,阿佩尔的方案更显得雄心勃勃。他想借助"先验论辩"来做更多的事情,以达到更实质、更宏伟的目标。而这恰恰是"先验论辩"所力不从心的。
止此,我们有必要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通过先验论辩实现的"终极奠基"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阿佩尔回答说:"在我看来,从所有哲学论辩的这一(蕴含的)要求中,我们可以为每一个人的长远的道德行为策略推导出两个根本性的规整原则:首先,在人的全部所作所为中,重要的是保证作为实在交往共同体的人类的生存;其次,要紧的是在实在交往共同体中实现理想交往共同体。"([1],第337页)这就是阿佩尔为终极的基础论辩所设定的两个实质性的目标。原则上这两个目标应该是从先验论辩中推出的。尽管很难推导出来。第一个目标是:我们借助科学技术的规范来营造合适的生存环境。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在科学时代,任何求助于科学手段的活动都同时包含着威胁人类生存的负面效应。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人们往往满足于现实的交往条件,对科学和文化的基础作出相对主义的论证。要想克服这一局限,还须预设第二个目标,即"解放"的目标策略。该策略只有求助于先验论辩才能形成普遍有效的制限条件,才具有康德伦理学意义上的"绝对命令"的价值。
在阿佩尔那里,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设想的关于世界一体化的共和理想,它的实现有赖于每个人所承担的共同责任。而对这种责任的意识只有通过先验的反思,从而摆脱了特定情境条件的制限才能达到。他的目标策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我们"总是巳经"处在一体化(包括经济与科技)的进程中了,也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受其前提条件的约束。尽管论辩的结论过于苛刻,但是我们认为,在方向上,阿佩尔没有错。
[参考文献]
⑴ 阿佩尔:《哲学的改造》,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版,第108页。
⑵ k.o.apel:"warum transzendentale sprachpragmatik?"in:h.m.baumgartner: prinzip freiheit. 1979, freiburg/münchen, ss.16-17.
⑶参见亚里士多德:topika, 101a20-101b.
⑷ 请参见拙文:"哈贝马斯的重构理论及其方法",载于《哲学研究》,1999年第10期。
⑸ h.krings:"die grenzen der transzendentalpragmatik",in: prinzip freiheit, 1979, freiburg/münchen, s348, ss.376-377.
⑹ 参见k.o.apel:the problem of philosophical fundamental grounding in light of a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of language, in:man and world, vol.8, nr.3, 1975.
⑺ p.f.strawson: individual,methuen, 1959, pp35-36. 另外也请参见作者在:"康德的先验演绎与自相关性问题――布伯纳与罗蒂之争",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6期一文中的讨论。
⑻ r.bubner:"selbstbezuglichkeit als struktur transzendentaler argumente,in: bedingungen der m?glichkeit, herausgegeben von eva schaper und wilhelm vossenkuhl, s.70.
方xx个体主义的三种诠释及其合理性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三篇
摘要:本文了对方个体主义的三种诠释:作为经济学模式的方个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模式的方个体主义,和作为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方个体主义。这些诠释反映了方个体主义既有其稳定的特质,也有其发展变化的方面。文章认为,方个体主义的某种合理性一方面体现为其独特的线路和解释功能,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对已有形态和特定局限的超越,体现为它与其它方的互动互补关系。这两种似乎相悖的合理性是方个体主义的真实境遇。它也说明方合理性的范畴本身不是一种绝对物,而是包含一定内在张力的互补性结构。
关键词:方个体主义 诠释 合理性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 which show that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 has both the definit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hanging aspects: the first as the ytic pattern in economics, the second as the ytic pattern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third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ytic pattern and value justification. the some rationalities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 consist in not only its ytic course and expository function but also transcending the existed conformation, and needing the other methodology as its complementarity. it seems contrary for the existence of such two kinds of rationalities, but this is just the real situation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 and it also reveal that the rationality of methodology itself is a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the intrinsic tension.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 explanation; rationality
方个体主义的著名批评者金凯(harold kincaid)说:“方个体主义在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中被广泛接受,但这一学说本身却很少被清楚地表述,事实上许多不同的思想都落在个体主义的名目之下”。wWW.meiword.CoM对方个体主义很有研究的霍利斯(m. hollis)也说:“我不认为个体主义是一个简单或明晰的题目。我以为,广义地说,一个个体主义者是把的优先性赋予单个代理(或他们的状态)的人。这种优先性可以是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或形而上的,也可以是伦理的,的或社会的。”[2]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对方个体主义的诠释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作为经济学模式的方个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模式的方个体主义,以及作为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方个体主义。透过这三种诠释,我们可以对方个体主义的合理性问题乃至一般方的合理性给出一种特定的理解。
一、作为经济学模式的方个体主义
方个体主义,国内由英文词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翻译而来。 关于这一术语的来源,马克•布劳格指出:“看起来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发明了‘方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的个人主义和‘上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的模式,这种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活动的试金石。”[3]布劳格的这一说明以马克卢普的论述为根据,后者曾引证说:“熊彼特是进行这种区分的第一个人,或者至少创造了这样一个必要的词来表达这种区分,因为他说过,是他提出了‘方个体主义’的名字”。[4]
熊彼特在《经济史》中,通过‘上的个人主义’、‘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和‘方个人主义’”的对比阐明了方个体主义是一种经济学的模式:
所谓‘上的个人主义’,我们是指经济政策问题上的自由放任态度。这种态度在德国被谑称为‘斯密主义’或‘曼彻斯特主义’。无论哪个经济学家,只要他根据有关单个家庭和企业行为的假设来建立其理论结构,就会被怀疑在颂扬他所描述的个人私利相互自由作用的结果。
所谓‘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是指十七和十八世纪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自我控制的个人构成社会科学的基本单位;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可分解成为个人的决定和行动,而对个人的决定和行动不必也不可能用超个人的因素作进一步的。这种观点就其隐含有一种社会过程的理论而言,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为了特殊的研究目的,也不允许从个人特定的行为着手研究,而非得研究影响这种行为的因素不可。我们可以家庭主妇在市场上的行为,而不研究影响这种行为的因素。由于不同社会学科的分工的不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这样去做,而不一定含有任何关于‘社会’和‘个人’的理论。由此我们便谈到了‘方上的个人主义’。那么,这个概念是怎样应用于那个时代的一般经济学的实际过程的呢?
可以证明,在主要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范围内,也就是在有关经济机制的逻辑性的问题的范围内,那个时期的理论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作为方上的个人主义来加以辩护,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就其本身而言,实质上并没有受到这种方法所固有的限制的损害。[5]
熊彼特这段话表明了以下三层意思:
第一,方个体主义不同于上的个体主义;
第二,方个体主义不同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即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个体主义;
第三,方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家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一种合理方法。
熊彼特对方个体主义和上的个体主义的区分,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赞许。他们认为这两者常常被混淆起来,而实际上“前者是从诸如自由对于人类进步和公共福利的贡献比其它任何东西都多的前提出发,得出一系列实用的断言;后者不做这类事情,不断言什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前提。它仅仅意味着在一定的经济过程的描述中,一个人最好从个体的行为开始”。(das wesen, p.90, 1908)马克卢普认为,由于熊彼特对这一概念的区分,“经济学理论可以运用坚固的个体主义的或‘原子主义的’的方法,而不需要使自己承担自由放任这样的纲领的负担”。[6]
熊彼特把方个体主义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区分开来,是他为保持方个体主义的合理性而设置的第二道防线。他认为,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内含社会与个人的一般关系,但它又主张只从个体出发去研究社会问题,因而是站不住的。与它不同,方个体主义不涉及社会与个体的一般关系,它在特殊的研究目的之下限于特定的学科,属于特定范围内的抽象,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熊彼特所说的这种模式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时所用的方法。当时,边际主义者用这种方法构造了比较完整的微观经济理论。熊彼特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一场革命。关于这场革命的方特征,门格尔作了如下的概括: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追求个体利益的动机,必须从这样的一般前提出发进行演绎推理,从而说明价格是如何形成的。熊彼特同意这样的概括,认为“1900年前后虽然尚未出现统一的经济科学,但已存在一种理论上的工具,其基本特征在各处是相同的”。基于这一点,可以认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所传授的,实质上是相同的学说”。[7]
熊彼特通过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进一步说明该方法的特点,其基本要点是:
1、对个体的描述是的出发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过正常商业生活的人”,他的行动会使满足或利润最大化;[8]人们“不同的需求给货物(goods)这个概念下了定义,并可以按一确定的(主观)重要性的次序予以排列”;[9] “随着我们所获得的每种货物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对每增加一‘单位’的欲望的强度则不断下降,直到达到零点”。
2、从上述描述推出下述定理:“为了从任何一能满足不同欲望的货物(包括劳动或金钱)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一个人(或家庭)必须这样分配该货物,即使其在每一用途上的边际效用相等”。进而推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一通用变换系数的特殊形式,经济现象的全部逻辑即从这个系数导出”。成本、生产、分配理论是“将边际效用原理的应用范围延伸到生产与‘分配’的整个领域。”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通过边际效用达到的新水平,边际效用原理只是它的特殊形式。[10]
如果上述表述还有难解之处,那么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就更加简洁:以偏好公理和效用概念表达个体的偏好性质和程度,使它具有逻辑一般的地位;然后在确定的约束条件下推出他的最佳需求,并把这些个体需求的总和视为市场的需求;最后,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达到了供给量与需求量的均衡点,形成市场价格。
上述的共同特征是:从个体的单子性质出发,逻辑地推出微观经济学的整个理论。
熊彼特和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方个体主义的合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已被证明是最有用的经济模式;其次,它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抽象和演绎方法。尽管它“不否认对个体的行为存在着强烈的社会影响,不否认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不否认社会实体对于社会学可能有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可以使用抽象获得了合理的立足点,所以可以不考虑上述因素。也因为此,它认定方集体主义“没有可以感知的优点”,“在经济中是多余的”。[11]
熊彼特的抽象还有其特殊性。按照他的方法,抽象的结果不仅是立足于个体的线路,而且也是特定的经济学视野。这是熊彼特视方个体主义为经济学模式的原因所在。他认为立足于一定的学科领域的研究,比较接近于自然科学的那种分科研究,也比较能够方便地运用自然科学中的还原论逻辑,其结果也比较容易得到辩护。这也是他回避将模式推广到社会科学的一般领域,也回避作价值辩护的一个原因。
虽然熊彼特认为这种方个体主义有他所说的这些长处,但体现为长处的地方往往也是短处之所在。作为一种方,把它限制于经济学领域无疑显得狭窄,而且人为地给予限定,理由并不充分。同时,排斥价值性的内容,把方个体主义的科学表述限于知识逻辑的范围,这一“观点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先驱者马赫、彭加勒和杜恒的影响”。[12]为了获取纯粹的科学性而回避价值性的内容,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社会科学与价值有没有确定的联系?如果有联系,那又如何对它进行刻画?这些问题摆在方个体主义面前,也为方个体主义以后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二、作为社会科学模式的方个体主义
实际上,方个体主义很快就跨越了它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的分界线,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模式。斯考特•高登指出这种情况:“‘方个人主义’一词最早由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他用此词意指正统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方规则。自从那以来它已经更为一般地被视为这样的学说:社会现象必须根据个体行为而解释。”[13]
方个体主义的这种扩展来自两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是经济学本身的膨胀。沙文(shaun hargreaves heap)等人认为,经济学家有一种学科性的“式的野心”,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模式扩展到其它研究领域。同时,由于经济学模式立足于对人的特性的一般概括,因而本身就存在着扩展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到20世纪30年代由莱昂内尔•罗宾斯作总结时,其基本任务已经变成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规定并没有把经济学研究限制于通常所理解的经济现象。恰恰相反,按照这一定义,经济学应当被运用于所有的人类行为。芝加哥经济学家盖里•贝克对此描述说(1976, p.8):
“的确,我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位置,在这里经济学方法是应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广泛性方法,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性的或不经常的决定,感情的或机械的终端,富人或穷人,男人或女人,成人或孩子,聪明人或笨拙的人,病人或临床医生,企业家或家,教师或学生。
“所以,‘经济学方法’不仅是一种精确的、通常也是稀缺资源配置的技术性研究,而且也是潜在的一种更为广泛的人类生活的范畴。如果后者显示了狂热的野心勃勃,那么它反映出时间、能量和感情是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资源。我们按照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对它们进行投资以获得最好的回报。如果我们所有的选择都具有一种广泛的投资效益结构,那么所有人类行为都可能让它的秘密服从于‘经济的’。”[14]
另一方面的努力来自经济学之外,是熊彼特所描述的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的影响。这种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传统,按斯考特的看法能够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霍布斯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现象能够化解为个人的行为,它必须根据支配个人行为的动机来。[15]到了穆勒这里,他将其表述为“社会科学中的化学的,或者实验的方法”:“社会现象的法则只不过是,也能够不过是社会状态中联结到一起的人类的行为和热情的法则。然而,在社会状态中的人们仍然是人;他们的行为和热情是服从于个人天性法则的。…社会中的人类所具有的性质只不过是他们原来所具有的那些性质,它们能够被分解为个人的天性法则”。[16]
尽管熊彼特对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提出了批评,但它作为一种传统仍然影响不衰。在社会学领域,韦伯说:“就社会学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它不会承认存在一种其‘行为’如同集合个性那样的东西。当我们在社会学的语境中,指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一支‘军队’或其它类似的集合体时,我们所指的仅仅是单个人实际或可能的社会行为的某种扩展”。“集合体必须唯一地被视为单个人特定行为的组合和组合方式。”[17]韦伯以此观点说明社会现象,强调社会科学家应当首先厘定历史的成分,在这些成分之间划出因果线条,使具体的结果归之于具体的原因。后来他又坚持“社会科学家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般可应用的理论系统,为此提出理想类型的使用类似于演绎经济学中的模型”。[18]这两个提法的逻辑模型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落脚于个体的解释。
沙文等人对理性选择概念的描述反映了相同的事实。他们指出,理性选择概念最早应用于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在这本书里,霍布斯把国家机构看作理性个体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免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危险而协议建立的。这种立足于个体选择的“社会契约”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的约翰•罗尔斯。沙文特别强调,这一传统不是源于而是平行于经济学在发展。耶利米•边沁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贡献超过了亚当•斯密。[19]上述两股力量推动方个体主义从经济学的模式转变为社会科学的模式。这种推动本身当然存在某种差别。来自经济学方向的,是经济学模式向经济学以外领域的扩张,其演绎性的模式并无变化;源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传统的扩张,既有应用领域的扩张,同时也有模式的扩展,它可能是演绎性的,也可能仅仅是因果性的。但是,它们的共同结果是,方个体主义很难再独守熊彼特所限定的经济学闺房。从1930年到1955年间,先是理性个体选择的形式公理理论,接着是博弈论,然后是公共选择理论,方个体主义作为理论实际走出了经济学的疆域。与此相一致,人们也更多地在社会科学的范围定义方个体主义。比如,波普说:“社会科学的任务乃是在以描述的或唯名论的词句来审慎地建构和社会学的模型;那就是说,是以个人的以及个人的态度、期望和关系等等的词句来进行的——这个公设可以称之为‘方的个体主义’。”[20]哈耶克也有类似的定义:“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它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21]
方个体主义的这种扩展表明,方个体主义是能够在社会科学领域被使用的。同时,这种扩展也产生了新的特征。方个体主义的模式从纯粹演绎性的扩展到演绎和因果并举,方个体主义的武器库有所扩充,而扩充的同时,逻辑性质也有一定的变化。不过,它也面临着实际的问题:这种扩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是合理的?
方个体主义的推广,与下面的一元论预设相联系: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普适的、唯一的科学方。根据这一预设,方个体主义就是普适的、唯一的科学方,它应该也能够面对和说明社会领域的所有现象。这一结论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由于它涉及了社会和个体的一般关系,因而受到方整体主义的挑战。方整体主义从相反的方向研究问题,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普适的社会科学方。第二,社会生活始终包含着价值,如果方个体主义能够面对社会领域的所有现象,那它必须把价值纳入自己的视野而不是排除在外。这就必须确定作为模式的方个体主义与价值是怎样的联系,以及在这样的联系中方个体主义将会有什么样的新特征。
三、作为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方个体主义
波普和哈耶克作为方个体主义者,其显著特点是确认方个体主义与价值辩护的联系,把对自由的辩护纳入论题的范围。布劳格对此所作的批评反映了这种情形,他说:“波普在这方面的区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为方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22]
实际上,波普和哈耶克的逻辑与布劳格的逻辑不属于同一类逻辑。他们的方个体主义既是社会科学的模式,又具有价值辩护的性质和功能,是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一种方。他们有两个主要的论证:一个立足于方个体主义的特殊性,立足于方个体主义与方整体主义的对立;另一个立足于方个体主义的一般特性,立足于科学与价值的一般关系。
第一个论证通过以下逻辑展开:方整体主义是专制主义的认识基础和理论来源,对方整体主义的批评和对方个体主义的维护,也就是对自由的维护;同时,方整体主义是一种类比性的生物学理论或有机体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个体自由为有机性所消解,因此反对这种有机的方整体主义,维护方个体主义,也就是维护个体自由的存在。
波普认为,方整体主义坚持认识事物和历史能够也必须从整体出发,这个整体是“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尤其它那各个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总和”。[23]正因为此,方整体主义获得了认识总体的绝对真理权,因而能够“从总体上重新设计社会”和“重建社会”。[24]由此,社会和人没有一个选择和道德决定的问题,自由在此没有应有的地位。同时,这种观点“强调社会集体和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认为“社会学像一切‘生物’科学,即一切研究有生命的物体的科学一样”,[25]把社会集体解释为生物的有机体,个体之间的关系解释为有机性的关系,从而使个体失去了他们的性、自主性和选择性。方个体主义与之相反,它不奢望对整体的绝对认识和完全控制,知道不可能有认识和社会运作的全能。同时,它不认为个体之间是有机体的关系,而坚持个体是一种体和价值源,一种具有活的精神的“原子”,从而保证了自由的本体性存在。
第二个论证认为,经济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出现,不是纯粹理性的产物。方个体主义作为它们的方,也是如此。哈耶克说:“经济从来就不是对于社会现象的原因的单纯智力好奇心的产物,而是一种强烈要求重建一个引起了人们深刻不满的世界的结果。”[26]波普也引用康德的话说明纯粹理性与价值选择的关系:“屈服于好奇心的每一种念头,让我们的探索热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并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这一点就表现了一种与学术研究相称的心灵的渴望。但是在所呈现出来的无数问题之中,要选择出那些其解答对于人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却只有智慧才能有此优点了。”[27]这里,智慧包含着价值判断。
波普认为,科学的社会获得和表达不是独断性的,而应当是自由精神的体现。自由的超越性也是科学的规定性,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以此为条件。他反对“社会科学的任务必然是做出社会的即历史的预测”[28]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没有给人的自由留下地盘,是“对科学方法的严重误解”。[29]科学所依据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无限理性,只有前者才能使自由的空间有可能保持,也只有自由和有限理性的适当结合,科学的发展才有可能。哈耶克从本体基础的角度进行说明:“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30]
上面的论证都是力图表明,方个体主义既是对个体自由属性的科学和抽象,又是对个体自由的确认和辩护。这种方个体主义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价值学说,但它打破了模式与价值学说两立的局面,确认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从而表明方个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方在特定的意义上不是价值无涉的。这一扩展改变了实证主义对方个体主义的限定,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当代的某种倾向。同时,这些论证也是对方个体主义更加全面的辩护。它强调,方个体主义的合理性不仅是认识上的(线路),也是价值上的(维护自由),而且还是认识与价值联系之中的(科学与自由的内在关联)。
然而,新的辩护并不意味着方个体主义确立了它的绝对合理性。实际上,波普的论证本身不具有完备性。他所批评的方整体主义只是一种绝对的、有机的整体主义。这种极端的方整体主义与自由的关系可能是对立的。但是,非极端的方整体主义却不一定与自由处于对立的状态。对这些方整体主义,不能排除它们也可以与自由具有一定的相容性或支持性关联。换言之,在方领域方个体主义仍然面对方整体主义的挑战,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根据证明自己是社会科学领域唯一合理的方。所以,问题可能转变为两个方面:或者方个体主义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论证,或者这一论断的前提就是可疑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一定存在唯一合理的方。马尔科姆•卢瑟福近期的研究试图表明,社会科学的方既不完全属于方个体主义,也不完全属于方整体主义,而是两者某些内容的结合或两者的互补。[31]方个体主义本身也存在着与此相呼应的调整,阿伽西的弱方个体主义已经承认和接纳了方整体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
实际上,从科学与价值的二元联结中把握方个体主义,不管论证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看法已多少冲击了社会科学是绝对一元参照系的观点。社会科学方法的一元论本身是简单性科学的结果,它的出现可能有助于认识社会科学的某些特征。但它把与价值的联系、把科学方法的多样性抽象掉了,因而使社会科学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特征。方个体主义的上述扩展,客观上是对简单性的扬弃,包含着对自身的某种超越。方个体主义和方整体主义可能都需要从认识和价值两个方面重新审视自己的前提,确定自己的地位以及与对方的关系。
总的来看,方个体主义的上述三种诠释,从经济学的模式到社会科学的模式,再到模式与价值辩护的结合,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落脚于个体的优先性或优越性。这一特征是方个体主义某种合理性的注脚,它体现为独特的线路和解释功能,体现为与自由价值的特定关联。但是,方个体主义上述的演变也表明,方个体主义的合理性又体现为对已有形态和特定局限的超越,体现为它与其它方的互动互补关系。这两种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是相悖的,但它却是方个体主义的真实境遇。它说明,方的合理性范畴不是一个绝对的同一物,它本身可能就是包含一定内在张力的互补性结构。
参考文献:
[1] harold kincaid.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atom[z].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edited by john b. davis, d. wade hands and uskali maki.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mpg books ltd, bodmin, cornwall, 1998. 294.
[2] martin hollis. of masks and men[c]. in 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history by michael carrithers, steven collins, steven lukes (ed).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25.
[3] [22] (英)马克•布劳格. 经济学方[m]. 黎明星等译. :大学出版社, 1990.55-56, 66.
[4] [6] [11] fretz machlup. methedology of economics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m]. acdemic press, new york, 1978. 472 ,472, 471-472.
[5] [7] [8] [9] [10]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史(第三卷)[m]. 朱泱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96. 208-210, 296-297, 206-207, 239, 240-250.
[12]bruce j. galdwell.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vol.i)[m].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rookfield, usa, 1993. 187.
[13] [15] [16]scott gord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m]. london: routledge, 1991. 651, 72, 652.
[14] [19]shaun hargreaves heap, martin hollis, bruce lyons, robert sugden & albert weale. the theory of choice—a critical guide[m]. blackwell,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1992. viii , viii-iv.
[17]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a].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v.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3-14.
[18]john watkins. ideal types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a]. in o’neill (ed.), modes of individuali and collectivi[c].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london, 1973. 145.
[20] [23] [24] [25] [26] [27]卡•波普尔. 历史主义贫困论[m]. 何林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19-120, 68, 58-59, 18-20, 51, 51.
[21](奥)a•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 贾湛等译. :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6.
[28] [29](英)波普.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 杜汝楫等译. 山西: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 364, 3.
[30](奥)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m]. 邓正来译. :三联书店,1997. 80-81.
[31](英)马尔克姆•卢瑟福. 经济学中的制度 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 陈建波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方xx个体主义与分析传统_其他哲学论文 第四篇
摘 要:方个体主义是传统与个体主义传统交汇的结果,这一背景特点形成了方个体主义的基本特征,使它与近代科学的传统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本文从自由原子论、并行的还原论和意向论,以及多线型的广义三个方面论述了这种关系,阐释了这种关系中的方个体主义具有特殊的表述空间,是一种包容性较大的研究纲领。文章指出了方个体主义的这一特点在当代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中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方个体主义 自由原子论 还原论 意向论 多线型
abstract: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 is the interactive result of both ytical and individualistic tradition, that shapes the character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 hence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 keeps the ytical tradition at an arm’s lengt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aspects of free-atomi, reductioni and intentioni, and multithreading-yses. it points out that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 i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rogramme in the relationship, which has special space of expression and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 free-atomi, reductioni, intentioni, multithreading-yses
方个体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方,而是一种包容性较大的研究纲领。wwW.meiword.cOm它的核心观点——社会集体的现象必须根据或落脚于个体的解释而得到解释——是基本的、稳定的,贯穿于该方的各个方面;同时这一核心观点又只是规定了从社会现象到个体的解释方向,而实现这一方向的方式却可以是多样的、可变的,能够基于本体论、还原论和意向论等给出不同的表达。
从背景的角度看,这样立论的原因在于,方个体主义是传统与个体主义传统交汇的结果。这种交汇作用形成了方个体主义的基本底色和特征,使得它具有特殊的表述空间。也正因为此,方个体主义中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方个体主义既不是纯粹的传统形态,也不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形态。如果从传统的角度看,方个体主义与它血脉相连但又若即若离。“若即”是指,方个体主义与近代科学的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直接表现是试图把个体作为原子纳入还原论的解释模式,而且这一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若离”是指,方个体主义不能不顾及个体的人文属性,给体现人的自由特性的意向论表达留下地盘。意向论模式虽然从广义上说仍然可以纳入的范式,但它毕竟又偏离了还原论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这种偏离不仅具有社会科学方本身的特殊意义,而且也与科学的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联系。当今方兴未艾的复杂性研究以还原论为研究基础又以超越还原论为其目标,方个体主义与还原论的联系和偏离,虽然并非就是复杂性研究,但却与它有着一定的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科学领域讨论方个体主义比仅仅讨论方法的运用更具有方的现代意味。
方个体主义的上述特点还应该放在下述两种对立的传统中思考: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图景是一种特别的盎格鲁—传统,其倾向是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元理论,如果不是看作等同,那也是看作是对自然科学的类似(本斯滕,1983和1935)。在欧洲大陆,社会科学则包含在人文科学中,即包含于geisteswissenschaften中,与naturwissenschaften 相区别。[1]这是两种社会科学概念,一则倾向于物的法则,另一则倾向于人的法则,表现了特有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又是相对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越来越需要一种融合性的新的社会科学概念。方个体主义虽然就其主要倾向看属于前一种传统,但它的包容性特点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具有某种一致性。
本文希望在这样一些背景视角之下讨论方个体主义与传统的关系。
一、自由原子论
方个体主义在本体论层面上是一种原子论,但是一种特殊的原子论。
方个体主义认为,社会中的个体与原子同处于本体性的地位。原子是自然的本体,个体是社会的本体,因此个体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原子,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原子。
原子论,历史地看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研究传统。它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把握:第一,它是一种与自然研究密切相关的自然哲学传统;第二,它是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纲领;第三,它是某种自然科学的具体学说。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同一个关于自然的理论传统的历史展开,其本体论意义虽有所不同,但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原子论一开始以始基论的形态出现,即把原子视为世界万物的始基。第欧根尼•拉尔修曾描述德莫克利特的学说:“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虚空,……原子在大小和数量上都是无限的,他们在整个宇宙中由于一种旋涡运动而运动着,并因此形成一些复合物:火、水、气、土。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某些原子集结而成的”。[2]按照这种思想,原子是万物构成和运动的基础。此后的伽桑狄在介绍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过程中使原子论的表述接近近代科学的形式。他说:“原子也是事物的元素。首先由原子组成最小的矿物质凝核或者分子,然后组成比较大的,再组成更大的分子,然后组成最小的,再组成比较大的和最后组成最大的物体。”[3]他的思想影响了化学家波义耳,后者把微粒作为一切变化的基础,提出了著名的化学元素论,因此引发了化学史上的一场革命。原子论进入了科学领域,但它的本体论的意义依然保持着。原子论作为科学研究纲领而取得卓越成效的例证是牛顿的微粒论。牛顿说:“整体的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和惯性,起源于粒子的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和惯性,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整体物体的全部最小微粒都是具有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并且具有惯性,全部哲学的基础就是如此。”[4]这里,原子作为本体,是所有事物属性的承载。
原子论本身虽然经历了历史的变化,但它的近代形态的本体论含义仍然可以概括如下:
(1) 世界万物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它们的最基本的单位;
(2) 世界万物的变化过程是由原子的结合与分离所决定的;
(3) 决定世界万物性质和过程的原子,其原质是相同的,只是形状、大小和数量不同。
这种概括对于我们认识方个体主义的原子论性质很有帮助。金凯•哈罗德曾经这样概括方个体主义的本体论命题:
“(1)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不存在超越个人之上的社会;
(2)社会过程完全由包含个人的过程所决定;
(3)所有个人的经济或社会的相关性质都是单子性质的,即其他人或社会实体,比如组织或机构都不介入这一性质之中。” 即使允许个人的非单子性质的存在,也只涉及它们的非本质的或外在的关系。[5]
从对比中不难看到,方个体主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原子论。
西方微观经济学可以帮助证明这一命题,因为它就是关于个体原子的经济学。它首先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经济行为,然后在此基础上单个市场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进而所有单个市场又是如何同时形成的。整个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个体的经济单位和变量,是个体的单子性质。西方主流经济学还企图把这种原则扩展到整个经济学。比较典型的奥地利学派把个体视为孤立的原子,认为这种原子就可以寻求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它企图排除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宏观经济学命题。
原子论所以能引入社会领域,有其历史方面的原因。乌•罗塞堡对此曾经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把原子论世界观中的一个单个原子的作用与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结构中的一个单个生产者的地位相比较,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虽然我们并没有以此而获得有关17世纪初期原子论复兴的原因的说明,然而,我们却看到,发展着的新型生产关系,给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们的自然哲学的抽象推论以一个完全另样的规模。我们在这个时期的物理学及哲学中,以断断续续的方式发现了生产者之间正在形成着的那些关系,发现了他们的日益增强的个体化及他们的可调换性。”[6]乌•罗塞堡把自然科学中原子论的复兴与社会个体的日益联系起来,把17世纪特定科学形态的崛起与当时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
个体这种原子地位的历史确立与个体自由历史发展的相互关联,从个体主义概念的形成也能得到佐证。据卢克斯考证,英文词individualiu直接从法文individualie 演变而来。他认为,个体主义一词在十九世纪以法文形式出现,用于概括启蒙思潮。19世纪20年代的圣西门主义者也用个体主义概括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正是他们把自由经济原则、社会的原子化和工业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哈耶克对此描述说:“‘个体主义’与这两个术语最初都是由现代的创始人圣西门主义者创造的。他们首先创造了‘个体主义’术语,用以描述他们所反对的竞争社会,然后又发明了一词,用于描述计划的社会。”[7]
个体的原子性质与个体的自由性质不仅有着历史关联,而且它们在本体的意义上就是相关的,因为个体本来就是一种自由的原子。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把方个体主义看作是一种自由原子论,这是它与自然传统的原子论的重要区别。
自由原子论的基本观点可以表述为:个体是一种主体性的原子,表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它具有主体能力,有自己的意愿、目标和认知能力,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特定情境中进行选择的能力;其次,它能够自主活动,具有自然原子不可比拟的活动空间和选择空间;再次,由于它能够在一种确定的意向和信念指引下通过其行为改变自己和环境,因而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原子,一种价值源。所以,主体性是个体的存在属性,自由就是其本体状态,这种存在属性和本体状态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得到扩展和增强。
方个体主义赋予主体性的这种存在以特殊的地位。从宏观的角度看,它使得社会与个体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不可同等而语;从微观的角度看,它限制了个体的进一步分割。
不可同等而语是指,个体自由的本体状态是真正的实在,而由个体组成的社会整体在此意义上却不是真正的实在。
在原子论中,原子与其所构成的物质层次虽然也具有不同的性质,但都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实在。与此相比较,在比较典型的方个体主义者那里,个体与社会却不具有这样同等的意义。韦伯曾表示,他一生都在为驱散“集体”的幽灵而奋斗。他认为:“就社会学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它不会承认存在一种其‘行为’如同集合个性那样的东西。当我们在社会学的语境中,指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一支‘军队’或其它类似的集合体时,我们所指的仅仅是单个人实际或可能的社会行为的某种扩展”。即使社会或集体存在的话,这种“集合体必须唯一地被视为单个人特定行为的组合和组合方式。”[8]一些著名的方个体主义者还从经验的角度对此论证。波普指出:“所谓的社会整体并不是经验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流行社会理论的公设……因此,对社会整体或集体的经验存在的信仰(可以被描述为朴素的集体主义)必须让位于这样的要求:社会现象,包括集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加以。”[9]哈耶克则以历史上的唯名论作为说明:“个体主义是哲学上唯名论的必然结果”。([7],p.6)唯名论否认“共相”的真实存在,认为一般名词只是加给一组事物的标记,不能成为感觉经验的对象。所以,只有能够成为感觉对象的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社会这些一般不是真实的存在。
个体与社会在本体上的不对等也体现在个体法则与社会法则的地位不对等上。穆勒说:“社会现象的法则只不过是,也能够不过是社会状态中联结到一起的人类的行为和热情的法则。…社会中的人类所具有的性质只不过是他们原来所具有的那些性质,它们能够被分解为个人的天性法则”。斯考特•高登对此进一步说:“这一命题在当代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形式包含在lionel 罗宾逊‘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论文’中(1932)”,在这一形式中,“经济学通过严格的演绎推理从前提推出它的定理,而它的前提是陈述人的天性的命题。”。[10]
方个体主义赋予主体性的个体存在以特殊地位的另一表现是,这种个体不能再继续分割下去。在古代原子论中,原子是构成万物的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随着近代科学的出现和现代科学的发展,原子被逐步认识到只是物质构成中的一个层次,它还可以继续分为原子核和电子等,而且这种分割并没有造成意义的断裂,也就是说,分割以后仍然属于物质的范畴。但是,在方个体主义中,个体的继续分割却造成了意义的断裂:分割以后不再属于人文的范畴。方个体主义在强调“大规模的社会现象都应该根据个体的情境、意向和信念来解释”[11]时包含着这些个体的主体性质具有基本的意义,如哈耶克所表达,人的知觉和信念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因而它构成社会科学的事实;社会科学的起点应当是这种事实,并由此构建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所以,知觉、信念这些主体特性与个体不能分离,个体以下的层次不再具有这种特性,分割只能到此为止。在这一点上自由原子论好像是对古代原子论的某种回归。
所以,方个体主义中的个体具有自然和自由的双重性质。正因为如此,方个体主义中的个体比原子论中的原子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方个体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社会领域的个体自由论。这正是方个体主义本体论的特点所在。
二、并行的还原论和意向论
既然方个体主义仍然是一种原子论,那么基于原子论的解释模式——还原论就同样适用于方个体主义对社会领域的解释;在这一方面方个体主义与自然科学方是相似的。另一方面,既然方个体主义是一种自由原子论,它的原子——个体具有特殊的属性,因此仅仅还原论又是不够的,于是有了意向论的解释模式。不论是还原论还是意向论,其解释线路都是从宏观到微观,使得社会的现象落脚于个体的一般或特殊属性,都是给出一个因果解释。从这一解释线路来看,还原论和意向论又都可以纳入的范畴,一种广义的范畴。
洛西(j. losee)曾从历史的角度说:“原子论的一个有影响的方面是这样的思想:根据在更基本的组织上所发生的过程,可解释观察到的变化。这个思想成为17世纪许多自然哲学家们的信条。亚宏观的相互作用引起宏观变化这一点被伽桑狄、波义耳和牛顿等人所肯定。”[12]这一信条首先表现为自然研究中的还原,主要有对象还原和理论还原。
对象还原是把所研究的对象从宏观层次还原到微观层次。这种还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宏观层次的质变还原为原子层次的量变”;另一种是“假定更深层次存在着同样的性质和过程来恰当解释某个层次的性质和过程”。([12],p.28)前一种可以称为还原论的间接形式,后一种可以称为还原论的直接形式。
间接形式在化学理论中有其典型反映。从化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拉瓦锡已经认识到:化学元素是化学所能达到的真正的终点。这一认识通过查里米亚•李比希的“当量比定律”和弗里契曼•普鲁斯特的“定组成定律”得到证实。1808年道尔顿在《化学原理新体系》中作出关于原子的基本论断,之后柏采力乌斯制定的“原子量表”,杜马发现的化学性质决定于化合物的“结构类型”,阿伏伽德罗关于决定元素原子结合数的“假说”,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律”,都以不同形式说明了在化学中物质宏观层次的性质是如何被还原为原子层次的量的组合形式的。直接形式在物理学中有其反映。牛顿“提出了一个研究纲领,来揭示支配物体微小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力”,希望“对短程力的研究将实现如状态、溶解、化合物的形成等物理—化学现象的综合,就象万有引力实现了地上动力学和天体动力学的综合一样。”([12],p.96)
对象还原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在方个体主义中都有体现。间接形式被方个体主义者确认为“社会科学中的实际发现”,而且经济学家指出的负反馈经济系统就是这样的发现。在这一系统中,个体动机是自利的,并非为了社会的利益,但是在相互作用中却达到了对社会有利的结果。沃特金斯强调方个体主义与这种间接还原的特殊关系:“我认为,在生物学者与方个体主义者之间具有真正的平行关系。例如,生物学家不用有机体中的大的目的论趋势解释怀孕中的大的变化,而用小的化学的,细胞的,神经学的等方面的变化作解释,这些变化没有一个与它们的共同的似乎有计划的输出有什么相似之处。”[13]方个体主义所以如此重视间接形式,是因为它认为这种还原在解释上是一种进展,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方个体主义也重视还原的直接形式。同样是沃特金斯,他赞成机械论原理,认为方个体主义与机械论是类似的,大尺度的社会现象必须通过个体的特性才能得到解释,社会的共同利益也就是个人利益的加总,个体性质的线性叠加就是整体的性质。经济学中“总需求是所有个体的需求之和”的命题是这种还原的直接体现。但是,他和波普对直接还原的某些运用持警惕的态度。例如,他们都反对心理主义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认为大规模的社会特性是相似的个人心理趋向的表现,即仅仅是个人特性的直接反映。他们认为这是把个人主义方推向极端,使得它在解释方面没有什么进展。沃特金斯认为,自从1714年曼德菲尔的《蜜蜂的神话》出版以后,个体主义的社会科学就把重点放在非有意的结果上,更加注意在特定的情境中自私的个人动机可能具有好的社会结果,而好的故意却可能有坏的结果。([13],p.740)理论还原在一定意义上能够看作对象还原的逻辑结果。牛顿说:“我希望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推理,从机械的原理推演出其余一切自然现象”。[14]]他将此推广至光学、电学、磁学、热力学、气体运动学等领域,形成了近代科学的谱系。这一观点后来继续被延伸:整个科学是一个等级结构,特殊科学在这一结构中可以还原到它们之下的更一般的科学,例如从社会学还原到心理学,心理学还原到生物学,生物学还原到化学,如此等等。理论还原不仅在自然研究和社会研究之间建立了理论的链条,而且也使自然研究中的理论还原成为社会研究中的某种范式。沃特金斯按照对象还原和理论还原的两分,也将方个体主义的规则分为内容和形式的两种。前者是一个特殊领域中某解释理论的前提内容必须满足的东西,称为规范原理;后者则包括逻辑规则和某些现实的富有成果的约定。
还原论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不是没有其特殊的限制。其主要问题是,作为原子的个体,当他的主体性活动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从而能够表现出重复性过程时,其所构成的现象能够以某些确定的规则为基础被还原论解释;但是当个体主体活动的自由度比较大,使得被解释的现象不具有可重复性的情况下,其解释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基础,这时意向论的解释就成为必要。
沃特金斯说:“社会科学家的立场类似于笛卡尔的机械论的立场。后者从不力图发现新的和闻所未闻的物理原理,因为他相信他拥有的接触原理是自明的最终原理。他的工作是发现典型的物理构造,该构造按照接触原理运作,产生可观察的自然规则。其理论模型体现了这样的规则,它们是‘自明’原理在某种假定的物理情境中运作的结果。同样,社会科学家在心理学方面也是依赖于熟悉的心理学的材料做类似的工作。他首先探查相关的意愿,然后发明简单而真实的模型以表明在精确的情境中,这些意愿是怎样产生某种典型的规则。社会科学家现在原则上能够解释这种规则性过程的历史实例,如果他的模型事实上确实适合这种历史情境的话。”([13],p.740)所以,对于可重复性的过程,从考察相关的意愿和情境出发,可以发现和确定某些典型的一般规则,通过它们逻辑地说明历史的情境。分配和交换经济学中的边际缩小效用原理,就是这样的规则。
但是在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中,由于不存在可重复性过程,因而不存在还原得以实现的逻辑基础,方个体主义只能以个体的意愿和信念以及他们所处的特殊情境来解释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沃特金斯说:对历史情境或连接情境的顺序的重构,是“揭示个体(通常既是有名的又是匿名的)以他们的信念和意愿(可能包括特殊的个体意愿和典型的人类意愿)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中是怎样产生要被解释的共同结果的。因为这一原因,我把侧重点放在意愿上,它是敞开的,似规律的”。([13],p.740)在这种似规律的解释中,意愿,特别是特殊的个体意愿具有特殊的地位,个体的自由属性在此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沃特金斯举例说,康斯坦丁大帝给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在意大利以广泛的世俗权力,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该事件可以作如下的意向论解释:康斯坦丁大帝具有使所有对手的权力服从于他的意愿;他同时认识到天主教不可能被摧毁,但如果使它成为皇帝官方宗教的话则能使它驯服,于是意愿与情境两者的结合导致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意向论的解释仍然可以视为性的,但这种性立足于人本身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是更加人文的性,而不是更加逻辑的性。这种情形在对方法的进一步探讨中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三、多线型的广义
相应于还原论和意向论的解释,方个体主义中的方法至少也沿着两个方向在运用。一是还原论的方向,经验加逻辑的方法;另一个是意向论的方向,人文经验的因果法。为了说明这种复杂情形,本文在此使用多线型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虽然方个体主义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定向,但沿着这一定向的线路是多样的。
首先从理性重建的演绎和非演绎性质来看这种多线型。
一词源自希腊文anàlysis——分解、肢解,指思想上且往往是现实的分解程序,它把事物、事物的属性或事物之间的关系分解为各个部分。笛卡尔对这一方法的描述也有这种意思:“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分解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15]
但是,近代自然科学中的方法,是和获取某种普适性和演绎程序联系在一起的。牛顿的目标就是应用方法归纳出解释性原理,而后以之推出理论的其它原理(定理)。这一方法在惠威尔那里有了更清晰也更形式化的表达。惠威尔认为“事实的分解是把复杂事实还原为陈述那些清楚而又区别的观念如空间、时间、数和力等之间关系的‘基本’事实。”“基本观念的意义可以用一组公理表达,这组公理陈述关于观念的基本真理。”“一个派生的概念仅当以理解这些公理的‘必然说服力’方式把它与基本观念联系起来时才被阐明。”([15],p.127-128)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是内含演绎于其中的方法。这一方法为后来的启蒙学者运用于心理学、认识论、宗教、历史、法、国家和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中,方个体主义中演绎性质的线路应该说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但是,方法并非仅仅以这样的纯粹形态存在着。在社会历史领域,许多时候在所获得的前提和被说明的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演绎性关系,至多说它们之间是一种因果性的关系。意向论的解释就是这样一种理性的再建。这种方法在社会解释中有很强的应用意义,在某些学科中与演绎性质的难分伯仲,在有些特定领域甚至是主要的研究范式。这些说明,社会的科学研究,很难仅仅诉诸于某一种线路。
多线型也表现在对经验的结果上,它们可能是某种一般原理,也可能是某些特殊之点。
与方法紧密相关的演绎虽然具有演绎论证的形式结构,但这时演绎前提的获得和性质发生了某种变化。前提是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获得的,不是先验的;前提可能具有公理那样的特性,也可能只具有一般假设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勒(e. cassirer)说:“牛顿的方法不是纯演绎方法,而是的方法”。[16]在这种方法中,经验是的基点。莱欣巴哈也说:“躺在原子论摇篮里的哲学思想,在19世纪这一百年中被实验所取而代之”。 [17]]这一点为哲学家从更广的视野所注意,卡尔纳普指出:“长久以来,各种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们都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概念和判断都是经验和理性合作的结果。”[18]就这种意义来说,科学是经验传统和逻辑传统“两个家族的联姻”。[19]在传统中,通过对经验的所获得的结果是某种一般原理。人们不仅可以对非生物进行这样的,也可以把生物,包括人在内分解为组成部分进行一般性概括。一旦人们理解了某一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如何运动及怎样被组成为一个整体,那么人们也就认识了处于其规律性关系中的生物。在启蒙学者的一些著作中,人类社会也可以被出这样的一般性前提,该前提被作为还原的落脚点。
但是,也有许多时候对人类的社会经验无法出这样的一般性原理。对于人类具体的意愿和信念在一定的情境下达致的结果,往往是独一无二的、不具有重复性的因果过程。对它的结果,显然不同于一般原理;人们能够厘定的是一些特定的意愿、信念和情境,只能由它们对特定的经验过程作出说明。有时候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复合性的,既有比较一般的人类意愿,也有特别的个体意愿,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说明某种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情形下,特殊的描述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多线型还表现在作为方法的多重背景理由上。
韦伯在1904年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的文章中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程序,在所谓更为普遍的法则之下系统地包容观察陈述和低阶理论。他强调社会科学家首先应该决定以什么样的观点去接近历史,然后厘定和描述它的成分,最终在这些成分之间划出因果线条,使具体的结果归之于具体的原因。但是,在他死后出版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中,他又坚持“社会科学家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般可应用的理论系统;为了达到这一点,他提出理想类型的使用类似于演绎经济学中的模型”。[20]沃特金斯反对早期韦伯而赞成晚期韦伯的观点。但是,即使他也承认历史解释中有不同的情形存在使得方法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他描述了三种情形:一种是束缚性解释,它通过追踪与其它事件的固有关系解释一个事件,并且在它的历史顺序中确定它的位置。大部分“文学的”历史学家事实上是这样写作的,在这种解释中理想类型不起重要的作用。第二种是原则解释,在一个简单的理想模型中从高度精确、高度形式的前提演绎出被决定的范围。这种理想类型可以证明某种原则在历史环境中发挥了作用。这是理想类型表现最为卓越的领域。第三种是细节解释。在这里理想类型大部分被特别构建,并在实施中逐渐现实化,直到它们成为经验的建构。([20],pp.154-159)上述三种情形表明,方个体主义作为方法,其不同线路的存在有其实际的理由。
方法在社会领域的多线型与它的对象——个体的人有着深刻的联系。如果人是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的某种统一,那么不同的线路可以看作向自然或人文不同方面的接近。可以比较粗略地说,还原比较偏向自然的一极;意向比较偏向人文的一极。前者逻辑性比较强,但具体信息损耗大一些;后者逻辑性弱一些,但具体信息的损耗似乎少一些。这些都是向人本身的某种接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其运用的合理性要视研究的对象和需要而定。
总的来看,四百多年来经典的性科学已经走过了辉煌的岁月,以致罗素能够自豪地说,“只有用才能有进步”。[21]方法的典型形态——还原论方法在自然研究领域所向披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种胜利也扩展到社会研究领域,方个体主义在主流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在社会学、学、心理学中的进军,程度不同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方法的胜利有其限度。它在社会领域的进军一开始就遇到了抵抗,特别是方法进入社会领域以后发生的复杂变异具有启迪性。社会领域的特殊性可能一开始就在提醒我们,经典科学的方法虽然在这里不乏建树,但新范式的出现在所难免,而且这种新的范式可能不会固着于抽象的唯一存在和客体化的形态,它可能更加逼近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这恐怕是我们在从方个体主义回溯到传统时应该看到的景象。
[参考文献]
[1] e.samuel overman, “introduction: social science and donald t. campbell”, donald t. campbell,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for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e.samuel overm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viii.
[2]《古希腊罗马哲学》(原著选读),“第欧根尼•拉尔修,第9卷,第7章”,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6页。
[3] 范•麦尔森:《原子——过去与现在》,弗赖堡/慕尼黑,1975年版,第130页。转引于乌•罗塞堡:《哲学与物理学——原子论三千年的历史》,朱章才译,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4] 转引自林定夷:《近代科学中机械自然观的兴衰》,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5] harold kincaid,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atom”,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edited by john b. davis, d. wade hands and uskali maki,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mpg books ltd, bodmin, cornwall, 1998, p.295.
[6] 乌•罗塞堡:《哲学与物理学——原子论三千年的历史》,朱章才译,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09页。
[7] a•哈耶克:《个体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译,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注。
[8]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v.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78, pp13-14.
[9]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7页。
[10] scott gord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652.
[11] john watkin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 a reply”, in o’neill (ed.), modes of individuali and collectivi,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london, 1973, p.179.
[12] 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13] john watkin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 and social tendencies”,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richard boyd, philip gasper, and j.d. trout,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91, p.739.
[14]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序言,转引于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48页。
[15] 笛卡尔:《方法谈》,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44页。
[16]〖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17]〖德〗赖欣:《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7页。
[18]〖德〗鲁道夫•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9]〖美〗m•怀特编著:《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7页。
[20] john watkins, “ideal types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 in o’neill (ed.), modes of individuali and collectivi,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london, 1973, p.145
[21]〖英〗伯特拉•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
西方传统知识论的延续与反叛_其他哲学论文 第五篇
摘 要:西方传统知识论的主流是实证主义知识观,这种知识观主要追求是知识的纯粹客观性、普遍性或说公众性、明示性等。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当代科学的发展,事实上打破了客观主义知识观一统天下的局面。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知识论,是对传统知识论的延续与反叛。
关键词:传统知识论 客观性 延续 反叛
知识与认识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说,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因此,它甚至被人们视为与认识相等同的概念。认识是在实践活动中,在与外界事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并发展的,是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知识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结晶(总结)。一般地,人们认为知识的体系就是科学,并把知识分为两大门类:其一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它是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总结,称为自然科学;另一是关于社会的知识,它是社会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称为社会科学。而严格地说,人类的知识实际上还包括哲学、音乐、艺术等不能归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的人文学科知识。
所谓知识论,在西方传统中,可以说是关于何谓知识以及知识何以可能的学问。作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论深受哲学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知识的本质属性进行了不同的规定,对知识何以可能作了种种说明,因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知识论,如客观知识论,主观知识论,人类知识论等。 本文所谓的西方传统知识论主要是指自古希腊至新老实证主义的知识论,以及继承了与之相同了诉求的知识论。后者如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或称为证伪主义知识论,虽然它主要是在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过程中提出,故而有与实证主义知识论相对立的倾向,但其主要区别也只是以经验的证伪原则代替经验的证实原则,其诉求实质上与传统知识论并无太大区别,所以也可将之归入传统知识论范畴。wwW.meiword.com不可否认,传统知识论有众多不同的学派或类型,然而它们却有以下一些主要共同点:一是其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追求知识或说认识结果的纯粹客观性;二是认为知识既然是纯粹客观的,那么它就具有普遍性或说公众性;三是认为知识是可以形式化、可以清楚地加以书面或口头表述的,即所有能称得上知识的认识都具有可形式化和明示性。
至二十世纪中叶,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等的新知识论兴起,西方知识论转向非常明显,新知识论显然不能归入传统知识论范畴,人们常以“后现代知识论”指称之。其实,由于这些新的知识论繁杂不一,如称之为“非传统知识论”也许更为确切。与科学哲学历史主义知识论同时对传统知识论反叛的,主要还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知识观和波兰尼“个人知识论”等。前两者都是对传统知识论的客观主义诉求加以解构,而波兰尼“个人知识论”则是在承认科学知识客观性的基础上强调其中的“个人性”,同时指出知识除了有可明示的部分外,还有不可明示的“意会知识”,知识(即使是科学知识)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波兰尼对传统知识论的延续与反叛或说扬弃已为新知识论——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论所认可与运用。
一
古希腊爱利亚学派奠基人巴门尼德提出的真理说开创了客观知识论的先河。他把哲学分为两种:一是真理的,另一是意见的。在他看来,真理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是一种仅仅凭其自身就足以保证成立,从而具有不容置疑性的认识。相反地,意见就是仅凭其自身不足以确定能否成立,从而不具有不容置疑性的认识。他认定认识的唯一出发点和途径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因为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p31) “可以言说、可以思议者存在,因为它存在是可能的,而不存在是不可能的。” [1](p31-32) “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存在者之外,决没有、也决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因为命运已经用锁链把它捆在那不可分割的、不动的整体上。” [1](p33) 因此“真理的力量也决不容许从不存在者中产生出任何异于不存在者的东西来。……要把一条途径当作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途径抛在一边(这确实不是真的途径),而把另一条途径看作存在的、实在的途径。”[1](p32-33) 巴门尼德所追求的知识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可以思议、言说的也即可明示的知识。但他的认识途径和知识论存在着明显不足,虽由后来的柏拉图以“知识就是人的灵魂对理念的回忆”的知识论加以补救,终因存在着把自足性、自在自为性作为知识的本质属性的缺陷而难以立足。
近代理性主义创立者笛卡尔认为,知识(真理)和意见相互区别的根本标准是“清楚、明白”。凡是清楚明白的认识就是知识(真理),否则就是意见。这也就说明,应将自明性视为知识的本质属性。笛卡尔还进而把“我思故我在”视为第一个自明的原则。他给出的理由是: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使我确信我说的是真理,而只是我非常清楚地见到:必须存在,才能思想;于是我就断定:凡是我们十分明白、十分清楚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2](p369) 这样的推断颇有“路灯下面找钥匙”的意味。 他一方面认定“我的思”和“思的我”是不容置疑的、自明的,因此就“可以把这条规则当作一般的规则。” “自我”的根本属性是思维,只要“我思”从自明的前提出发,经过严格的逻辑演绎推理,所获得的知识就具有客观实在性。另一方面,他也许觉察到了仅仅在“路灯下面找钥匙”是不够的、是不妥当的,于是又补充说:“不过要确切地看出哪些东西是我们清楚地想到的,却有点困难。” [2](p369) 他最后干脆坦白:“然而我以前曾经接受了许多东西,认为是非常确实、非常明显的,可是我以后却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可疑的、不确实的。” [2](p373) 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只好打出上帝的招牌来担保自明性和客观实在性之间的普遍必然性。他说:“我方才拿来当作规则看待的那个命题,即‘凡是我们清楚明白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其所以可靠,只是因为有上帝存在,因为上帝是一个圆满的实体,并且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从上帝而来。由此可见,我们的观念或概念,既然就其清楚明白而言,乃是从上帝而来的实在的东西,所以只能是真的。” [2](p377) 康德认为,笛卡尔虽然把“自我”视为知识的条件,并指出知识是经由“自我”而达成,但这个“自我”只是经验的“自我”,从这一“自我”出发不可能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这已为英国经验论者休谟所证明。康德于是创立一种“先验知识论”,把一切知识归结为某种“先验的”或“先天的”原则及其产物。这里所谓的“先验知识”并非时间上在先之意。就时间先后而言,他认为在经验之前,我们是没有知识的,一切知识都是自经验开始。他还指出:“经验就是现象(知觉)在一个意识里的综合的连结,仅就这种联结是必然的而言。因此,一切知觉必须被包摄于纯粹理智概念下,然后才用于经验判断。在这经验判断里,知觉的综合统一性是被表现为必然的、普遍有效的。”[3](p284) 在其知识论中,构成人类经验和知识的形式和原则,同时也就表现为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界”的秩序和法则,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作为经验的对象之物,其必然的合乎法则性是先天地被认识的,而先天的纯粹理智概念使普遍有效的判断成为可能,是可能经验的先天原则。我们的理智法则不是从自然界中得来,相反地,却是理智给自然界制定出法则。他指出:“一切经验的可能性的先天原则也将会恰好被规定为一种客观有效的经验知识。因为这些原则不过是把全部知觉(按照直观的某些普通条件)包摄在上面所说的纯粹理智概念下的一些命题而已。”[3](p282) 总之,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保证不在于“经验自我”,而在于“先验自我”的纯粹理智概念,知识因而是由先验的自我应用纯粹理智概念统摄现象而形成的。每个人用相同的先天的认识形式去统摄同一个对象,当然会获得相同的知识并因此具有客观性。他的整个知识论正是围绕纯粹理智概念而展开的。笛卡尔、康德的知识论虽然属于主观知识论,但是,追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或说客观性、明示性仍是其根本目标。
二
自孔德以来,西方主流知识论是实证知识论,也就是实证主义的知识观点。实证主义是一个相当繁杂的哲学学派,可大致分为以孔德等为代表的早期实证主义、以马赫等为代表的中期实证主义和以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原子主义),石里克、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后期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在休谟知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证知识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科学知识都是实证的知识,只能满足于对经验现象的描述;一切超越经验现象的认识都是“形而上学”,必须予以排斥,等等。他明确指出:“实证哲学的根本特点正是认为人的理性必然不能说明一切高不可攀的玄妙奇迹。”“我们认为探讨那些所谓始因或目的因,对我们来说乃是绝对办不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4](p28-30) 他进而极力主张要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科学,同时把实证的原则和方法贯穿于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之中,从而建立起实证的“社会科学”或“社会学”。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也说:“我将把所有那样的一些命题叫做形而上学的,即这些命题宣称表达了某种在全部经验之上或之外的东西的知识。例如,表达了事物真实本质的知识,表达了自在之物、绝对之物、绝对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知识。”[5](p215) 他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知识。由于不能表述经验内容,不能为经验所证实或证伪,因而也就没有科学的功能和知识的价值,因此,形而上学的命题和陈述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实证主义学派涉及的人物和思想众多,但其根本观点和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由于认定科学只是限于经验范围之内,只是满足于对经验的描述和整理,所以才是实证、确切和有用的知识,而哲学中的那些有关客观存在的判断和普遍的因果性、必然性命题都超出了人类的经验,因此也就非我们的认识能力所及,从而都是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毫无意义也毫无必要加以探讨,应该将之拒斥于科学知识之外。结果,知识几乎就等同于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又被认为只能满足于对经验的描述和整理,必须得到直接经验的证实,超越经验以外就不会有任何科学和知识。实证主义在西方产生了长期而巨大的影响,到马克斯•韦伯那里,科学又被进一步确信为“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被认定只具有工具合理性,只是通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控制外在世界目的的有效手段。他断言“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进而主张科学家要“为科学而科学”,并且“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6](p37-38) 这样,不仅科学知识本身是价值中立的,而且科学活动的动机、目的都只在于科学自身,与个人价值毫无关联。从此,实证主义的“知识就是实证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是纯粹客观的”观点更是空前泛滥,并且导致了种种严重后果。这也就是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所指出并予以尖锐批评的现象。他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而“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的事实的科学”就会导致危机,“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7](p5)
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知识论有逐渐转向人类知识论的趋向。从这一角度而言,后期维特根斯坦已把生活形式看成了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的根据。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把知识看成只是能够导致成功的信念,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可归结为在经验上具有某种使用效果的东西。他指出,康德把信念和知识加以严格区分是既无必要又无根据的,所谓知识就是信念,科学知识的基础在于感觉经验,知识只能是经验的知识。因此,他认为根本不存在有普遍原则或客观规律性的知识,知识本质上是由经验所造成的一系列信念。信念作为一种思想、一种道理,自然是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人们寻求知识其实就是寻求和确立稳定的信念,这是思维或认识的唯一职能。他指出,我们的思想的唯一职能就是产生信仰,一切与信仰无关的东西,都不包括在本来意义上的思想之内。而只要达到一种坚定的信仰,我们就会十分满足了,不管这个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还断言,我们所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去寻求这样一种信仰,而且关于这种信仰,我们以为它是真的。他一再申明,知识、真理的标准就是能够指导行动并取得实效,它们以探究共同体而非以个人的意识为根据,一致性是知识客观性的保证,这种一致性的根据就在于探究共同体。为了避免走向完全的相对主义和唯我论极端,皮尔士对自己的真理观进行了规定,他说:“所有从事研究的人所终于要一致同意的意见,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 [5](p150) 后来的实用主义者詹姆士没有就此打住,而是进一步发挥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效用原理和意义理论,从而得出了“有用即真理”这一众所周知的结论。大体上说,维特根斯坦从人类学的立场来说明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皮尔士则从人类行为、生活的角度来解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此后的实用主义基本上坚持了这一知识论范式。
胡塞尔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意义的建构,因而把西方传统哲学主要问题,即如何把握外物与观念、自我与他我的统一根据问题视为意义及其主体间性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而建构意义的最高、最普遍的根据就是“纯粹自我”。在他看来,所谓知识的客观性是指对一切人都有效,而不仅仅是对单个的自我有效。如果从诸我共同体的角度来建构意义,那么所建构起来的就具有主体间性,即对每个主体都普遍有效。主体间性意味着对个人有性,从而对个人有客观性,而它不仅属于我,还属于别人,因而是非个人的。知识是由主体建构的,其客观性也就是显然的。胡塞尔持有一种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科学观,但是这种对立主要是在于研究对象和范围上。他批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残缺不全的概念”,因为实证主义主张只研究纯粹客观的事实,而排斥一切有关主体的所谓“形而上学”问题。胡塞尔则主张科学应以全部的存在者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即科学研究不仅要包括客观领域,而且要包括主观领域的东西,有关意义、价值和理性等问题都应成为其对象。因为在他看来,实证主义限制科学的任务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拒斥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拒斥科学本身;抛弃作为普遍的、科学的、哲学的观念,将导致科学研究内在动力的丧失;抛弃理性的、普遍的哲学的理念,必然导致欧洲的人性危机。可见,胡塞尔所要反对的并不是实证主义把知识视为纯粹客观的观点,而是反对将科学的任务仅仅局限于经验的、客观事实的研究。实际上,学自然科学出身的胡塞尔对于精确的自然科学一向十分景仰和赞叹,他希望能建立起一种真正具有自然科学的严格性的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是他一生从未改变的哲学主张,也是他终身奋斗的目标。[7](译者的话)
与维特根斯坦、皮尔士相似,胡塞尔也把生活世界作为把握自我的一个必要环节,从而使其知识论向人类知识论靠拢。然而,无论是维特根斯坦、皮尔士,还是胡塞尔都未能从唯物史观有关“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基本观点出发,因此其知识论只是一种准人类知识论,而不可能达到主义知识论的高度。与传统知识论一样,他们所追求的知识的可明示性和客观性也仍旧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当代西方知识论由于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等的创立而有所发展,但仍无根本性突破。四
从以上所述可见,西方传统知识论有这样一种信念:认识主体所直接观察到的是世界的外在表现,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潜藏于事物内部的,正像一个苹果,苹果核心在里面,而外面是苹果皮。黑格尔因此明确指出,事物的直接存在,就好像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在寻找这个潜藏着的本质。西方传统知识论尽管具体的学派有多种,但是,总的说来,追求纯粹客观的真理性认识却是一致的目标。从古希腊至今,人们认为,主体与客体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之间有明显可分的界限;认识过程是一种严格遵循排中律、不矛盾律的二值关系的反映;认识的结果——知识应当是纯粹客观的,是客体特性在主体观念中的直接再现;对于认识结果的真理性评价必须以客观性为尺度。因此,西方传统知识论总的说来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实证主义的,归结到一点就是客观主义的。“知识是客观的”的观念在当代的哲学家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如波普尔就以《客观知识》指称自己的知识论。既然知识是客观的,那么它就具有普遍性,就是公共的,人们常说的人类知识宝库就有这个意思。反过来说,既然是“知识”,它就应该具有客观性,就与个人无关,并且必然是可以言说或说可以明示的;既然是“知识”,就不得超越经验,并须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如果知识与经验相冲突,人们就须随时准备将之抛弃。
20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非经典物理学的崛起,事实上打破了客观主义知识观一统天下的局面。人们对微观高速领域物质对象的认识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仅是主体能动活动的结果,而且在这种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主体影响和客体特性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样的分明和清晰。事实上,即使是在宏观低速的情况下,认识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像微观高速条件下的影响那么显著而已。因此,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其纯粹客观性便成为大可怀疑的。
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在军事和工业中的应用日益增强,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日趋严重,人们对此已无可回避。特别是核战争、基因工程等将对人类的生存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因此“科学家自身开始对研究者的职责和无限地追求真理的权利提出批评和表示怀疑。”[8](p84) 传统知识论的“价值中立”观已难成立。现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和社会事业,科学发展已无法离开社会的资金、资源的支持,并最终要为此做出还报,一般都属于某个机构或组织的成员或雇员的科学家仅凭个人兴趣“为科学而科学”已经不太可能。早就说过“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亦即当我从事那种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作为人而活动的。”[9](p75)科学家从事所谓绝对客观的学术研究活动,实际上无不受世界观、价值观等影响以及社会环境的制约。
科学知识的客观主义立场和原则,20世纪中叶起遭受了众多学派学者的猛烈挞伐。根据其针对传统知识论的不同侧面以及采取的批判方式特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是直接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种思潮或学派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的库恩、费耶阿本德等、持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罗蒂、利奥塔等、还有知识社会学学派……。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利奥塔的观点和对科学客观性的否定已为人们所熟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也是最为强劲的力量之一,在这一学派看来,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其研究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的建构而已。换言之,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并非科学家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并且通过各种修辞手段使之得以认定为普遍真理的局部知识,是负载着认识和社会利益或受到特定社会因素塑造的。像其他知识一样,科学知识实际上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就有了“科学知识是制造而来”的观点,直至以《知识的制造》或《制造知识》来表明自己的知识观。 传统的科学知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家对自然界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客观反映,科学从而就具有无可置疑的客观真理性、普遍性等特征,科学知识社会学走的是一条对这种知识客观主义诉求加以直接否定的路,或者说,知识社会学是通过解构的方式来消解知识的客观性,宣称科学知识来自于科学家在社会各种因素影响下的建构,甚至是压力下的产物。“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这一条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受到了多方质疑。
对于传统知识论的反叛的另一类型是波兰尼所走的道路,即认定知识是个人的。波兰尼指出,认识是一种艺术,其中有着不可抹煞的主体性因素,虽然不可否认外部世界的“秩序”,但是,同时亦应肯定通过人类认识可获知的“外部规律”中渗透着的人类生活意义,这种意义既非机械决定论又非主观目的论的,人类的认识活动建基于个体的技巧,以达到“意会整合”,即确定科学明示预测与实际感觉经验是否相符。在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怀着责任感和普遍性意图而进行认识活动,其行为遵从或取决于支援背景,并与某种隐藏的现实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预示着范围不定的、依然未知甚至是依然无法想象的真实的隐含意义。作为认识的过程和结果的任何知识,其客观性以现实性为基础,但其中又离不开其支援背景,这种支援背景与现实的联系就是知识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与“个人性”相结合就是所谓的“个人知识”。[10](p460)它企求的是要从否认知识的普遍性、公众性,从而否定其纯粹客观性,达到修正传统知识观的偏颇的目的。可以认为,知识社会学派是从传统知识论的“外部”,而波兰尼则是从传统知识论的“内部”打破知识是纯粹客观的神话。后者否定知识的纯粹客观性,同时又强调其非纯粹主观性,而是客观性与主观性(个人性)的结合。
概而言之,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库恩、费耶阿本德等、持后现代科学观的罗蒂、利奥塔等,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知识观,以及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都可以说是对传统知识论的一种反叛,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还是对之扬弃与发展。20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非经典物理学的崛起,以及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日趋严重事实的公认等,成为这些知识论出现的现实根据。
五
人类已经逐渐步入知识社会,这一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不同的时代,社会追求知识的目的有所不同。按维娜•艾莉的见解,人类社会历史大至可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有三种追求目的:在工业革命以前为第一阶段,那时对知识的探索纯粹是为了知识本身或启迪智慧,为知识而求知、为学术而学术;第二阶段大约始于1700年,求知目的的实用性倾向逐步加强,实用功利性的知识日益受到重视;大约从19世纪80年代之后为第三阶段,以美国工程师泰勒首创工业生产流程科学管理方法为标志,这一阶段意味着开始将知识应用于知识本身、利用知识把现有知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11](p21)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新知识论也已应运而生。这种知识论对知识的概念及划分范围都予以了扩展,使人类对知识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对知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功能有了更为深刻理解基础上,人们对知识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也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关于什么是知识,托夫勒曾说过:“我们所说的‘知识’是指被进一步融入一般性表述的信息。”他认为知识的内容应包括“信息、数据、图像、想象、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社会象征性产物。”可见,托夫勒所称知识的外延是十分广泛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也给知识下了一个定义。它引用在20世纪60近代西方关于知识的“4个w”,即知识可以分为四种:一是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what),指人类对某些实际存在的事物如某地的土地面积和人口状况等的基本属性、特点的认识和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的掌握;二是关于原理和规律的知识(know-why),即对某些事物、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和规律的认识;三是操作性的知识(know-how),指能够转化为人的实际行动,以便实施某项计划和制作某个产品的方法、技能和诀窍等等的知识;四是有关产生源头的知识(know-who),指有关知识的来源和产权归属关系的知识,即知道是谁创造或生产了某些特定的知识。吴季松认为,在此基础上,应再加上know-when和know-where才更为准确。因为即使知道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谁来做,但是如果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来做,仍然会产生错误。吕献海认为,不管是历史上还是今天,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曾经在大至安邦定国、小到家庭生活中把一件好事在错误的时间或地点做成坏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知识大的时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谁”、“在哪里”,都是极为重要的知识。所以赞同吴季松的见解并认为,“6个w”才可以说是准确的知识,虽然可以说“知道是什么”之中就包括了“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但还是强调一下when和where两个w,把真正的求知看作“6个w”更好。[12](p27-30)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知识的概念比信息要宽得多。信息一般只包括知识中的know-what和know-why范畴,这些也是最接近市场类型的知识。
通过对知识经济条件和情景下知识结构的研究,人们把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编撰知识”(codified knowledge),一类是“意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前者主要是指能够以语言和图形的形式进行系统化处理的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也就是“明示性知识”;后者则主要是指在生活实践中摸索积累起来的难以用语言来加以清晰表达的知识,即“非明示性知识”或说“隐含经验类知识”,上述“4个w”中的“know-how”和“know-who”即属此类知识。世界经合组织在《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事实上,人们所拥有的知识明显地要超出人们能用语言诉说的范围,必须承认和强调“不可明示知识”的实际存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所理解的知识不仅表现为语言,还表现为能力。这种能力是处理可明示知识的能力,作为知识它显得更加重要,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如果把明示性知识视为需要转化的原材料,“意会知识”则可以视为处理这种原材料的工具。所以,知识经济的知识论既重视明示知识又强调利用或驾驭这种知识的能力,后者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 可见,人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波兰尼关于知识划分的意见以及“个人知识论”的有关观点。知识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知识论,是对非传统知识论尤其是对波兰尼知识论的肯定与运用,从中我们看到了其对西方传统知识论的延续与反叛、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巴门尼德.论自然[a].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c].:商务印书馆,1981.
[2] 笛卡尔.谈方法[a].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c].:商务印书馆,1981.
[3] 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a].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c].:商务印书馆,1982.
[4] 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c].:商务印书馆,1964.
[5] m.怀特编著,杜任之主译.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c].:商务印书馆,1981.
[6]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m].上海:三联书店,1998.
[7]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8] 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9] 卡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出版社,1975.
[10] 波兰尼.《个人知识》[m].贵阳:贵州出版社,2000。
[11]维娜•艾莉:《知识的进化》,珠海出版社1998.
[12] 吕献海编著.《知识——高科技与知识经济》[m].: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
波兰尼的科学人性化途径_其他哲学论文 第六篇
摘 要 波兰尼以“意会认知”理论变革实证主义科学观,透过意会认知的三位体结构和内居运行机制,可知所有知识都无法摆脱主体性,都属于“个人知识”。因此,研究事实的科学和研究价值的人文学其意义都为人所赋予,其中并无谁优谁劣的问题,两种文化或说科学与价值由此得以融合。波兰尼似乎为萨顿科学人性化的主张寻到了一种具体途径,然而,他的理论虽说必要却不充分,要实现萨顿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5 )是英国著名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在国际哲学界,他主要以创立意会认知(tacit knowing)理论而著名,这一理论作为科学人性化途径的有益探索和尝试,至今已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和重视。科学人性化的首倡者为科学史家萨顿,这一主张的实质是要使科学与价值融合,消除c.p. 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的鸿沟”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对立的现象,他又称之为新人文主义和科学人文主义,并认为达到这一理想的途径是科学史。他为科学史的创立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获得了卓著的成就,被公认为伟大的科学史学之父。然而,事实证明,科学人性化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而且,萨顿的科学史途径并非他所声称的那样是唯一和有效的途径,他的理想至今也尚未实现。[1]尽管如此,萨顿的科学人性化主张却为世人所肯定和称道,一些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积极响应他的号召,竭力寻求科学人性化的具体途径,波兰尼和马斯洛就是其中之二,两者都图求建构某种理论框架,以实现萨顿所树立的目标,马斯洛从人本主义心理学角度,而波兰尼则从认识论角度出发进行探索。Www.meiword.cOM本文只能简略地涉及波兰尼的有关理论。他通过批判实证主义错误的科学观,证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知识一样,充满人性因素,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人化的科学,是一种“个人知识”,在非言传的“意会认知”层面,科学与人文是相通的,一切知识都离不开个人,离不开意会的估价。因此,从本质上说,“两种文化”的对立是虚妄的,他认为自己所创立的“意会认知”理论,可以变革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达到科学人性化的有效途径。
一、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
萨顿对于科学与价值的批判,主要侧重于科学远离人性和“两种文化”对立现象,波兰尼则更深入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从而着重批判实证主义科学观。
波兰尼指出,近代科学既对人类知识、道德,以及社会进步起着主导作用,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谬误,实证主义的怀疑论即为其中之一。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实证主义就着手排斥、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知识,视自然科学为超然、客观和唯一可靠的知识,从而产生了如下严重后果:这次大战直接摧毁了启蒙运动唤起的人类道德无限进步的信念,而科学理性主义盛行又导致了人类乃至整个世界意义的丧失,亦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令世界“祛魅”。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是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两种主要和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还原主义的方法被到处滥用,人们相信并在实践领域,尤其突出的是在生物学领域以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生命过程,而物理学和化学又可以用微观粒子之间的作用力来阐述。而没有看到“生命超越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际。[2]因此,一切生命和人类本身及其一切成就,包括诗歌、艺术、哲学思想等都可用这种方式解释,科学的理想素来就是拉普拉斯式的理想:用原子运动知识取代一切知识。科学对宇宙的说明都是机械论的,在“奥卡姆剃刀”挥舞之下,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一切所谓价值和道德观念,质言之就是所谓“意义”在整个宇宙中都无处存身,都被消灭殆尽。波兰尼称这种还原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化约主义”,它虽然铺就了现代科学之路,但却剥夺了事物的意义,并使我们有关人的观念走向歧途,即把人化约成没有知觉的自动机器,或化简成一团欲求,这就不再可能承担人之所以为人的责任,科学家及科学的利用者就不必再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科学与道德的分离因此势所难免。波兰尼指出,面对当代的种种道德危机,即使我们并非熟视无睹,“但是,机械性的方法已经把我们在学术里所追求的事物和这些道德问题分开,使学术的事仅止于‘学术’而已”。([3],p.24)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无所作为。更为甚者,客观主义又将科学认知过程仅仅视为“可观察事实的集合”,排除一切主观因素, 科学成为纯粹客观的产物,凡与之不符者皆被视为无科学性而遭抛弃。 客观主义将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性视为科学乃至一切真理的标准,否定人在科学中的参与作用,因此人的价值和评价在科学中再也不可能有其地位,这就必然造成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人性的,最终是对人自身存在的否定,并使人的本质发生异化。波兰尼指出,自我标榜为“精密科学”因而控制一切知识的自然科学,已成为当今种种危险谬误的最大甚至唯一源头,这种状况甚至比宗教教条控制一切知识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宗教教条毕竟只是许多谬误的来源之一。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实证主义传人亦不得不竭尽全力来拯救或重塑道德及其标准。“但是,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科学一日仍是知识的理想、超然一日仍是科学的理想,伦理就一日难保不被怀疑论的怀疑完全毁灭。”([3],p.30)可见,实证主义已完全无可救药,如果不从根本上对这种科学观加以变革,而只在局部上修修补补,终究是无济于事的。
波兰尼进一步批判道: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还原主义科学观只能导致科学蒙昧主义,“假使拉普拉斯式的期望或是一个类似的对准确科学的理想果然证明自身就是人类知识的全部,那将是迫使我们完全无知。”([3],p.36)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科学客观化,使科学远离人性,它貌似增大了科学理论的可信度,实质却是令科学变成了与人无关的神话!
二、“个人知识”和“意会认知”
科学作为人为和为人的事业,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人性因素,正如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无论是科学的起因,还是科学研究的过程,都离不开个人的兴趣、热情、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离不开个人的信心和技巧。波兰尼指出:“科学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而得到运用。正是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运用,科学家才形成科学知识。因此,我们通过研究技能的结构可以了解科学家的个人参与的本质。”[4]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有充足的证据显示,纵令使用高度自动的记录仪,我们也无法排除可能影响一连串读数的个人偏见。”“没有一门科学能够预测观察到事实,要能如此,除非怀着信心去依赖一种技巧,即凭借训练有素的眼、耳以及触觉上的精妙,去确定科学的明示预测是否与实际的感觉经验相符合。”波兰尼断言:“知识的取得,甚至于‘科学的知识’的取得,一步步都需要个人的意会的估计和评价。”([3],p.34)因此,我们有必要“犯禁”,要对传统科学观予以彻底的翻转,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塑造知识时的贡献加以考虑,并入知识的观念之中,彻底地以一种个人知识的概念代替时下流行的、超然的观察的理想。”([3],p.32)质言之,就是要变革科学观,不仅要承认主体性或曰主观因素,而且,要更进一步地承认,包括科学在内的“知识的形成取决于认知者的个体活动”科学是人的,特别是个人的。波兰尼因此将自己最重要的论著以《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命名。马斯洛称这是一部伟大著作,它作为在科学领域的反映,很好地阐述了新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5]
为了阐明“知识是个人的”论断,波兰尼首先将人类的全部知识加以类分。按照他的方法,“人的知识分为两类。通常被说成知识的东西,象用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的方式来表达的东西,只是一种知识;而非系统阐述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如果称第一种为言传知识,第二种为意会知识,就可以说,我们总是意会地知道,我们在意知我们的言传知识是正确的。”([6],p.6)一般人总以为言传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全部,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个小尖顶,而意会知识却是隐匿在水下的宏大部分。与言传知识相对应的传统认识论,所依靠的是可明确表述的逻辑理性,而在波兰尼看来,人们恰恰长期地忽视了意会知识及与之对应的意会认知,它乃一种与个体的认知活动密不可分、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的隐性认知功能,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内在本质,它所倚重的是一种隐形的理性。为了说明科学中存在意会认知和意会知识,波兰尼就行为主义学习心理学对获得似真性(plausibility)描述进行了考察。他发现,这种描述显得很“客观”,却已经是极力加以简化了的,其所以为人们接受,是由于所用语词都指归于心中暗存的心理事件,从而使其意义被意会地理解和把握。否则,这些“客观”描述将毫无意义,并且也不会达到目的。([3],pp.370-371)他坚信,意会认知对于科学发现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科学与人文整合的研究有着重大的价值。在其宏篇巨制《个人知识》中,波兰尼详述了意会认知的结构与运行机制。他一反将科学认知视为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规律的反映论观点,指出认知是一种艺术,尤其指明科学是人的艺术,其中有着不可抹煞的主体性因素,虽然不可否认外部世界的“秩序”,但是,同时亦应肯定通过人类认知可获知的“外部规律”中渗透着的人类生活意义,这种意义既非机械决定论又非主观目的论的,人类的认知活动建基于个体的技巧,包括以上所说的“训练有素的眼、耳以及触觉上的精妙”等,以达到“意会整合”,即确定科学明示预测与实际感觉经验是否相符。在波兰尼看来,个体正是通过这种技巧而达到对知识的直觉体悟和洞知,言传知识总是言犹未尽的,或说简约化了的,而先于语言和逻辑解释的意会知识其意境更为丰富、具体和本真,因此,意会认知结构才成为人类认知理性的真正本体。科学的真正动机来自人类个体对美和善的追求,意会认知无疑是依存于人的,它依赖人类个体身心的体悟,属于一种内在的、隐性的逻辑理性,它只能是个人的,与之相对应的知识即是个人知识。
科学知识何以是个人的?波兰尼指出,若不否认科学是以我们对自然界的融贯性辨识力为基础,那么,科学发现就如同感觉行动中视觉及其他感官在生理层次上所作的辨识一样,必须依靠一些非形式的力量,以引导科学研究并为其结果提供判别的标准。他说:“科学家有能力猜出那些是反映事物本质的现象,这种能力之有异于我们平常的知觉能力,正在于其能够以常人知觉无法去妥善处理、整合所遇到的现象。”[7]可见,把科学视为纯属依靠理性并获得纯粹客观的结果是错误的。波兰尼还进一步指出,无论整合结果是建立知觉或认知事实,还是产生想象的作品,其过程基本上都是非形式的,其中亦就暗含着许多非逻辑的意会性的东西,比如信念和直觉等。他说,“科学所进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便是基于运用众多微妙的启示及其引导的直觉,而对事物及现象可信性的估计。”[8]可信性甚至权威性是科学理论等成果为世人接受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显然是非客观因素,波兰尼因此认为,外行人之所以接受科学陈述,所根据的并非自己的观察,而是承认科学家在专门领域中所具有的权威,甚至某一科学家对另一科学家的成果加以利用,情况亦复如此。科学刊物采用稿件时也取决于建基在科学家们对事物的性质,以及可能产生科学成果的方法等根本信念上的可信度。其中的信念并没有严格和明显的形式,在形成判断过程中只意会地起作用。[9]因此,包括科学在内的认知过程,与非个人的纯粹客观观念完全不同,它“始终(从选择问题,乃至证实发现)植根于个人的意会整合行动,而不是立基于明示的逻辑运作。依此而论,科学的探讨乃是一种具有动力的想象发挥,而且植根于认定以及对事物性质的信念。”科学的理想是要发现“意义”,“而不是把一切化简成没有意义的一团原子,或化简成偶然发现的力量的平衡”。([3],p.75)为此,波兰尼曾提出“理智的感情”(intellectual passions)概念来解释科学活动,它所指的是科学活动过程不仅存在逻辑等理性的、客观的因素,而且渗入了价值关怀,审美体验等人文内涵或说主观因素。[10]把科学在内的知识视为个人知识,“对于我们理解知识以及我们相应地评价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6],p.14)
意会认知的基本结构由三个中心组成:一是支援性成分;二是焦点目标;三是将两者连接起来的认识主体。这三者是一个由认识主体人控制的三位体,主体人的控制体现于正是他把支援成分加以整合并指归其注意力的焦点,使之成为一个焦点目标。当认识主体将注意力焦点集中于他物时,所产生的与此事物相关的意识,是意会认知的基础,波兰尼称之为支援成分与焦点目标的“功能关系”或“转悟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建立了对支援者的“转悟知识”,即“关于对建立焦点目标似乎有功能的支援者的知识”。意会认知就是转悟认知,正是由于这种认知,使我们在观察某一事物时,“有了感官知觉所不会有的真正新颖的感觉质地--由感官知觉所意会地创造的质地。”([3],p.33)波兰尼称之为“现象变化”,这是转悟认知的特征之一。它的另一特征是:当支援者指归一个焦点目标时,所指归的焦点目标就是支援者的意义,因此,指归便是意义赋予的过程。认知主体既可以给诸支援成分赋予意义,又可以通过特殊的行为消除意义,并破坏意会认知的三位体结构。具体而言,这种行为就是观察方式的改变:只要他把焦点注意力从焦点目标转向某些支援成分即可。举例说,当我们在黑夜以拐杖寻路时,有三个中心,一是握杖及拐杖触着障碍物时由拐杖传到手掌而引起反应的经验;二是由我们以杖端指向路面的注意中心即注意焦点;三是将此两者整合起来的主体即我们自身。简单而言,我们是以对握杖的注意和触觉经验作为支援,以碰着障碍物的杖端及其指向的路面为注意力焦点,寻路过程就是转悟认知过程,其中的“现象变化”表现为:拐杖与手掌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意间被忽视了,主体“变成”了感觉到触碰障碍物的杖端。这里所谓的“现象”并非感性意义上的,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念性“本真现象”。由杖端感觉所获取的信息就是主体从拐杖所获取的触觉经验意义,正是这意义使我们得知所观察到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把焦点注意集中转移到手握拐杖的感觉等支援成分上,探路运作就会遭受失败,因为此时相应的意会认知三位体被消解了。张一兵先生曾以“庖丁解牛”为例解说这种三位体结构及其动作方式,这是十分确切和精到的。[11]此外,还有走钢绳、弹钢琴、以电脑或打字机写作等,其中所有的技巧施展,都是转悟认知,都存在类似的三位体结构和认知运作。同样,如果要消解这种三位体,就都可以将焦点意识转移到脚、或手指及有关技巧即步法和指法,以及对相应物件的控制等支援成分上。个中缘由何在?波兰尼认为,在意会认知过程中,我们对于焦点目标和支援成分的的意知程度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注意某种另外的东西(b )而相信我们意知了某种东西(a)时,我们不过是对a的附带理会。因此,我们集中注意的东西b有a的意义,我们集中注意的对象b通常是可以辩认的。这两种类型的意知相互排斥:当我们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直附带意知的东西时,它就失去了附带的意义。”([3],c.2)这里的b是指焦点目标,a是各种支援线索,ab 两者相应的意识即支援意识和焦点意识是互不相容的。属于支援成分的事物,作为支援意识层次上的意义是存在的,但一旦主体将注意力集中于它们时,它们却变成了焦点,故而使原有意义丧失,露出了其“硬生生”的物质本质,这就是说其作为支援意识的属性已为焦点意识所取代,造成了“意义的剥夺”,进而造成三位体的崩解。
从此可见,认知主体人在其隐性的背景线索(背景知识、经验和技巧等)的支持下,功能性地指向焦点时,认知行为才会整合地发生。波兰尼将这种三位体的结构推而广之,并进而将意会认知视为一切认知皆然的认知方式,他说:“一切知识不是意会知识,便是根植于意会认知,两者必居其一。”([3],p.72) “缺少个人、意会的知识,化学、生物学以及医学课本将尽成空话”。([3],p.34)
波兰尼进行科学人性化途径的探索,无非是要使“意义”赋予科学、赋予全部知识直至整个世界。换言之,就是令科学、知识乃至世界“返魅”。因此,他特别看重“意义”概念,可视为其哲学理论缩影的重要著作就命名为“意义”。在此,我们还应特别了解一个有关的重要概念。波兰尼指出,在意会认知过程中有一种“接合意义”产生,它无法以逻辑明示,而只能以“想象”获取,上述的“意义剥夺”中的“意义”可以说指的就是“接合意义”,我们可从下例中进一步把握其含义: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注视本国国旗时,我们心情异常激动并怀有一种神圣感,这绝非仅仅那块布所能导致的结果。毋宁说,在我们注视国旗时,所有有关的、支援性地指归于它的事物都为我们所意会地知觉到了:祖国的存在及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伟大的、悠久的传统文化、壮丽的山河以及我们对它的无限深情,甚至可以随时为它献出生命。这些都成了这面旗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言以蔽之,国旗象征着国家。因此,我们注视它就会意会到其神圣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所谓的“接合意义”,它并非一块布本身所固有,而是在转悟中整合建构而来,是主体人“想象”和“赋予”使然。若我们去除一切支援意识,这种意义就会荡然无存,这块布亦就只不过是一块布而已。可见,接合乃一种意义建构,是功能性地形成的特殊意境,是靠背景知识和经验等支援线索意会地、而非以某种明示框架去刻意建构出来。三、意会认知机制的具体运行方式--内居
波兰尼指出,意会认知是以“内居”(dwell in )的方式运行的,也就是说认识主体通过同化于众多的支援成分而达到与认识对象融为一体,达到神交的地步,此时,认识主体进入了被探索事物的境界,意会整合于是得以进行。无论是对于数学、物理、生物和化学等自然科学,还是对于诗歌、艺术和神话等人文学来说都是如此。内居,不仅是意会认知主体融入对象的过程,而且也是对象向主体归化的过程,即内居是双向性的,在主体客体化的同时,客体也主体化。这里所谓的主体化或客体化主要是指客体或主体具有了对方的某些属性,而非指它们在认知过程中的地位对换。主体内居于对象体现为主体遵循支援意识的引导,投身于对象之中,与之“欢合神契”。例如,若要了解某一个人,我们就要十分投入地“扮演”他,“变成”他,进入他的处境,用他的观点去判断他的行为,亦就是进入我们平常所说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境界,从对象的立场和思想观点出发,以其思维方法去观察和思考,最终达到对其深刻的认识和完整的把握。这也就是马斯洛论述的创造性活动中人应达到的境界:人与其世界的融合,即人与对象同构、相互匹配或互补,融为一体。从此就不难理解“如果你要画鸟,就必须变成一只鸟”这句话。[12]反过来,对象内居于主体即表现为认识对象亦同化于主体,“成为”主体本身或“存在于”于主体之中。上述例子中,当主体“变成”对象即他人,以他人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和思考时,实际上,那个具有个性的对象,就已“变成”了认识主体,即客体已归化于主体之中。
波兰尼作为一位物理化学家,自然能够深刻理解微观领域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的关系,也就是波尔所强调的“在现实的舞台上,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内居”概念是波尔的话语转换及其观点的扩展和运用。双向内居的结果已令认识主客体的关系趋向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境界,正如天地人浑然一体中的物我相融一样,意会认知中的主体和客体已难解难分。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二者已经互相同化到毫无差别的地步。教育中有“寓教于乐,寓乐于教”一法,其中的“教”与“乐”互相“寓居”于对方,但两者并不等同,其差异性仍然保持着。意会认知中的主客体关系正类似于“教”和“乐”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状态下,主体才能更彻底、更真实地把握客体。显然,这种状态不仅非内居之前就存在,而且还非一次内居就可达到,而是经过多次、持续不断,步步深化才能达到的境界。波兰尼明确指出,主体人与对象相对时,首先形成一种“我一它”认知关系,这是一种外在的、理想化的、比较肤浅的层次,人们此时以为可以排除一切人为因素,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或说客观真理的绝对把握。但当意识到其荒谬性,认识到所有知识皆个人知识或植根于意会认知,认识主体的背景知识框架、信念、情感和价值观皆起作用,进而通过内居运作之后,“我-它”关系就逐渐向“我-你”关系转变,最终达到主体和对象一致的“我-我”境界。波兰尼认为,通过对“我-它”和“我-你”关系实质上植根于主体对自身的“我-我”关系的意知,“我-它”和“我-你”之间的鸿沟就得以填平,如此,意会认知理论就建立了从自然科学不间断地过渡到对人性的研究。[13] “我-我”是内居的最高层次结果。然而,若要更具体地明示意会认知过程,把整合步骤一一阐明却无法做到,因为正知波兰尼所说的,我们是内居于支援成分之中,内居于对象和事物的根据之中,并以此为标准或规则去注视对象和事物,因此就无法对之一一加以指认。况且,一旦注意焦点转移到支援线索上,其原有意义就会被剥夺,从而破坏意会认知的三位体结构和运行机制,认知运作就无法进行。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能依靠可以明示的逻辑,唯有凭借我们的想象跃过逻辑的裂隙,才能达到对一个焦点对象的整合,这是非逻辑和无可确指明示的过程,故而只能意知。([3],p.73)
四、内居--两种文化鸿沟的桥梁
波兰尼认定内居具有普遍性,他声言:“凡是认知,都是个人参与--透过内居而参与。”([3],p.50)并以大量篇幅论证这一断言。在《意义》一书中,他就论证了在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诗歌、艺术、宗教、神话乃至日常生活常识中,内居皆作为意会认知不可或缺的运行机制。由于意会认知三位体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由于注意焦点一旦转移到支援成分,就会造成意义的“剥夺”,进而导致三位体的崩解和认知运作停顿。因此,即使从数量上有可能找出全部的支援成分,但从本质上却不可一一加以明示。相应地,整个意会整合的过程也是不确定、无法确指的,若想强行对这一过程和步骤明示出来,终遭失败。尽管如此,这些支援成分的存在及其参与知识--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学知识的形成或获取过程却是无可置疑的。从此,拉普拉斯式的科学理想、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其病症便有救治的良方:承认一切知识中的个人性,一切知识若要完整,就必须有个人知识,必须有主体人内居于物,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人性即主观因素。通过内居而来的知识概念,“初步连接了科学知识、态度和方法与人文知识、态度和方法的鸿沟。”亦就是说,内居铺设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因为认识到个人参与是普遍的认知原则,把握了意会认知结构及运行机制,我们就会将人类的行为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评价为有知觉、有智慧、有道德责任的人类行为。同样,用作为科学的意会认知方式和人文概念对人类及其行为进行研究,所获得的人文知识亦就不能说是不科学的。波兰尼或许意识到仅仅由内居而断言任何知识具有“个人性”还是不够的,本来还应进一步证明这些“个人性”到底是如何参与认知过程、如何起作用才算彻底。但更进一步地明示这一运行机制的步骤又不可能,因为如前所述,它是非逻辑的,只能靠想象。波兰尼的策略因此变为论证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等一切知识都离不开想象力的作用,他特别指出要更正人们已有的偏见:处理事实的科学不需想象,而处理价值的人文学则全凭想象,并由此导致科学是纯粹客观的,而人文学则成为全无客观根据的臆想的错误观念。波兰尼论证道: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学都需要想象,都具有客观性,只不过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从此可见,以事实和价值二分法定性和区分科学与人文学知识已不适当。当然,这并非说两种知识的意义全无差异,而是说,既然它们在本质上都牵涉到个人的参与和想象,那么,由科学所整合或说创造的意义就不见得更真更优。反之,亦然。他说,人文意义,对于我们的生命乃至整个世界,亦有着巨大而无可否弃的重要性,而非像实证主义者所指责的那样是虚妄的、应排除的东西。错误的传统科学观念一旦变革,“科学就不会好像是要我们以超脱的方式去研究人与社会,而且,我们将会复归到自身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的地位。”([3],p.50)科学、人生乃至整个世界因此就充满了意义,也就达到了当今的后现代科学思潮所追求的世界“返魅”的目标,也就是实现了科学人性化的理想。
五、波兰尼途径的评析
波兰尼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集于一身的学者,对实证主义科学观所造成的危害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他对机械原子论和客观主义僭妄的批判也是有力的。他一反科学是客观的、普遍的传统观念,利用逆向思维提出了科学乃至一切知识都是个人的,这不只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要走向另一极端,其深层意义是通过证明科学和人文知识都离不开个人的参与,从而达到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充满人性因素的认识,以促使人们科学观的革命性转变。从意会认知理论,我们极自然地想到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两者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具体的事例可举如:波兰尼的“支援线索(成分)”和皮亚杰的“认识图式”都考虑了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如价值观、审美观、个人兴趣等在认识过程中的参与作用。波兰尼的双向“内居”运作、“接合”、“整合”和皮亚杰的“同化”、“协调”、“平衡”等概念亦有着相通之处。而且,从总的方面看,两者都是对主体内部认知机制的探索。一般认为,皮亚杰的研究侧重于借助逻辑方法,将个体的认识发展视为自我运动过程,视为一种内化的逻辑过程,因此其注意力便主要集中于探索这种内化的机制,虽然他的“认识图式”主张考虑审美、道德意识等非逻辑的、人为的因素,但实际的作用机制未见得已经探明,而且对社会环境和实践因素的影响未曾引起足够的重视。[14]因此,皮亚杰的理论是有缺陷的。波兰尼强调认知尤其是意会认知过程中支援线索的决定性意义,并声言这种支援线索包含一切主观人为因素。因此,知识甚至是“个人的”。他强调主观性的作用确实有着充分的理由。但是,意会认知的内居机制是特殊的,到底哪些支援成分起作用,又如何起作用即内居的进一步机制、步骤如何?这都是无法靠逻辑推论并予以明示的,只好求助于“想象”的“非逻辑一跃”。于是,他转而要做的工作便是证明“想象”的普遍性。最后,他给出如下结论:凡是整合,都必须依靠想象力,而且有待整合的成分差异愈大,所须的想象力就愈丰富、愈宏大。([3],p.165)我们认为,波兰尼的论说也并未因此就算彻底,它仍然令人觉得是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再者,“两种文化”的对立,科学给人类带来危机,其原因复杂多样,不仅有科学观等认识论方面的,还有社会历史方面的根源。他的意会认知理论是建立在较为狭窄的范围上,尤其是建立在许多重大因素未能加以具体考虑的认识论范围内,这就难免其局限性。退一步说,即使从认识论上解决了问题,从观念上解决了问题,亦并不就等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不能说只要沿着波兰尼的途径行进就可实现科学人性化的目标。但是,波兰尼毕竟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一名得益实证主义方而有所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在不消解科学客观性的前提下,能够肯定并着力证明科学中的人性因素,并进而声称科学是一种“个人知识”,确实有利于变革冷酷而僵硬、与人性毫无关涉的实证主义传统科学观,为沟通两种文化,为科学人性化迈出了必要的一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参见黄瑞雄《萨顿科学人性化的理想与现实》,《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4期.
[2 ] m.polanyi:life transcending physics and chemistry.1967. see: knowing and being,ed. by marjorie grene, univ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3] 波兰尼:《意义》(meaning),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
[4] m.polanyi : personal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49.
[5] 见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3页脚注。
[6] 《波兰尼讲演集》,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
[7] m.polanyi: science,faith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24.
[8] m.polanyi:the growth of science in society,minerva 4(summer 1967,pp.533-543). see also m.polanyi: criteria fo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ublic policy,and national goals.ed .by edward shils,cambrige,mas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68,pp.187-199.
[9] m.polanyi:science:academic and industrial,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metals89,1961,pp.401-406.
[10] see m.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london,1962,
pp.132-202.
[11] 张一兵:《波兰尼与他的‘个人知识’》,哲学动态,1990年,第4期。
[12] 见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云南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13] 参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论。
[14] 可参前苏联奥布霍娃《皮亚杰的概念--赞成与反对》,商务印书馆,1988年。以及周文彰《狡黠的心灵》,中国大学出版社,1991年。
[15] m.polanyi: the logic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
[16] m.polanyi:the study of 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17] m.polanyi:the tacit of dimens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1966.
[18] m.polanyi:beyond nihil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卡尔·波普尔和卡尔·xxxx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七篇
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在世界范围的实验,及其后来的挫折。当然,人们可以说:严格地说来,遭受挫折的不是一般的,而是特殊模式的。然而,根据70年的经验重新审查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原是合情合理的。除此以外,也要求重新审查其他学派对主义的批评,看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本文将审查卡尔·波普尔的批评以及他所提供的替代办法。
在他的思想自传中中,波普尔描述了主义在他生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他与主义的邂逅是他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事件之一。正如他所说的,这使他成为可错论者,认识到教条思维与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主义和弗洛伊德、阿特勒的工作一起,帮助他解决了“分界问题”:科学陈述的特点是它们对经验反驳和批判评价保持开放,换言之,它们应该是可证伪的。波普尔虽然从此以后成为主义的批判者,但他对个人和主义仍怀着尊敬。他写道:“主义的人道主义动机是无可怀疑的……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将理性方法应用于社会生活最迫切的问题……他并没有白费心血……”[2,v.2,pp.81-82]“回到前主义的社会科学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了。所有现代学者都应归功于,即使他们不知道他……甚至他的错误的理论也是他的不可战胜的人道主义和正义感的证明。”[2,v.2,p.121]“的信念基本上是开放社会的信念。”[2,v.2,p.200]
波普尔认为,的社会理论可归结为两个主要学说: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www.meiword.CoM按他的意见,主义的和其他的社会理论家信奉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使他们不能提出可证伪的社会理论。那么,什么是历史决定论呢?
历史决定论
按照波普尔的意见,历史决定论主张:“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根据历史规律提供给我们长期的历史预言。”[2,v.1,p.3]或者说,历史决定论是:“对社会科学的一种探讨方法,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历史预见,认为这个目的可以通过发现历史演变背后的‘节奏’或‘模式’,‘规律’或‘倾向’而达到。”[3,p.3]
根据这些和其他段落[2,v.2,p.82,86,106,136,319],历史决定论可用以下论点表征:
(1)社会科学方法是历史方法,是一个研究历史的问题。
(2)研究历史能够发现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规律。
(3)这些规律形成“预言”的基础,即关于社会发展未来进程的可靠预见。
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的这一表征隐含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以下意义上有根本的区别:
(1)自然科学规律是普遍的,如牛顿的运动和引力定律,但社会科学规律则不是,仅适用于特定社会。其逻辑结果是,没有普遍的历史规律为社会提供预见。
(2)社会不能归结为个人及其关系的集合。说“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是这些个人所在的关系的总和”[4],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并不能为从事该行为的个人所意识到。
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一区别使有关社会和历史的陈述免遭证伪。从一个社会取得的证据不能用来反驳有关另一社会的任何陈述。它也使人们能够在理论上将一个完美的社会描述为一个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理想。由于这一点,历史决定论一般与某种形式的乌托邦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社会科学没有普遍规律,历史决定论者只是试图确定社会将采取的发展方向。他们常常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正如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必然会摧毁自己。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对社会未来的长期预测是社会研究的中心。
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解释,至少对主义是欠公允的。和他的许多支持者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而他们确实主张社会科学中有普遍规律,如在所有社会生产力适合生产关系的规律,以及所有人类社会都要依次通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然后主义社会。人们可以争辩,这些规律在社会中是否存在,但是不能否认主义者确实主张像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中有普遍规律。另一方面,波普尔自己一些陈述使人认为事实上他也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例如,波普尔强烈反对还原论[5],然而他又主张方个体论,即认为有关一个社会的事实总能用一系列个人的行动来说明,这样他就是一个社会还原论者,我们且不管一个社会是否完全能用个人行动来说明。波普尔指责主义不可证伪也是如此,这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但是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与乌托邦主义有亲缘关系似乎是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的论证。
可证伪性
波普尔的基本论点是,不可能用科学或任何其他理性手段对人类历史作出预见。这可能意味着,这些预见是不可证伪的。然而,主义假设,所有人类社会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和主义社会可以是高度可证伪的和严格的普遍概括。后来,波普尔反对对历史事件作出科学预测的可能性,他依据的事实是这种预见或语言可能是错误的。理由是,历史决定论者赖以作出预见的证据并不能有效地保证预见的真理性。因为如果我们根据观察到不同社会演变的类似性而提出一个假说,我们并没有理由预期历史的发展会继续产生这种类似。如果我们在一定的时期内观察到某种模式或倾向后提出,这种模式或倾向是某一社会的普遍特点,那么,正如波普尔指出的,一种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倾向,会在几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波普尔对历史预见的可错性的论证是有道理的,但这结果是意味着:历史的预见,同科学中的任何预见一样是容易证伪的和可错的,这样他指责历史决定论不可证伪也就不能成立了。
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是根据它所说的“发展规律”其实不是规律,而是外推到未来的“倾向”,而倾向是依赖于初始条件的。[3,p.118]波普尔认为,在自然或社会世界中所有的进化系列都有由种种初始条件决定的特点。然而,如果初始条件改变了,那么进化也会采取完全不同的途径。从本世纪初开始的主义运动的涨落本身似乎验证了倾向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论点。
波普尔基于预测有可能错误而提出的反对有可能对历史事件作出预测论证,是自我拆台的。如果这些预测有可能错误,那么这意味着从中作出预见的理论是可证伪的。而预见的失败并不总是提供强烈的理由来反驳从中作出预见的理论。根据预见的失败而修改科学理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仅当理论的支持者坚持正确应用理论不可能发生错误时,预见的失败才成为反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主义者,而只有教条的主义者才坚持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主义的预见是模糊的。他们勾划出一个发展的轮廓,而并不提供发展的细节或时间表。这样,就没有确定一个何时预见失败构成反驳的时刻,而理论就会被认为是不可证伪的。但主义者可以争辩说,历史的发展并不要求完全精确的规定时间的预见,而只有一个社会要达到的总目标才能预先确定,细节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再加以确定。
乌托邦主义
然而,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提出的最决定性的反证是在他的[3]中提出的。这个论证是:“由于严格的逻辑理由,预见历史的未来进程是不可能的”,因为: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到人类知识的强烈影响。”
(2)“我们不能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
(3)“所以,我们不能〔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3,pp.vi,vii]
波普尔在这一点是对的:我们仅能在数字或字母系列中,根据对该系列的元素的概括对该系列的后续元素作出可证伪的可检验的预测。但在人类历史的系列中则不能:因为这里存在着知识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以及知识增长的不可预测性。
许多忠诚的主义者为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和的理想社会而斗争,但他们混淆了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规律。他们预设,科学和人都是万能的,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人能够根据科学规律来确定地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然而,科学规律并不能帮助我们预测人类的未来,也不能预测科学本身的未来。例如人们可能没有考虑到:
第一,需要和要求总是不断扩展的,尤其是因技术的进步而膨胀。技术的进展能够有助于满足人的需要,但是同时它又极大地人们的需要、欲望和要求。当中国开放她的大门、引进先进技术后,人们就不再满足于收音机了,他们需要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小到大,从老式到新式。但任何新产品,当它开始研制、开发、试销时,都是不多的。这样问题就来了:谁应该先获得它?因此,任何社会,尤其是技术不断日新月异的社会,都不可能使所有产品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第二,人不是制造出来的产品。他们不是一样的,也不可能使他们成为一样。每个人有23对染色体,每条染色体上面有5万到10万个基因。人是这些基因与他或她所处的复杂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任何社会都不能使所有人都愿意和能够做到尽力而为。
除此以外,在几乎所有的或前国家中主义者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预见:忽视了市场和在社会、经济和生活中的作用,夸大了阶级斗争,低估了社会或民族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他们根据这些错误的预测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导致运动的挫折。
整体论
在个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一些主义者和波普尔也许都只把握了一端。波普尔争辩说,历史决定论不能说明当社会体制改变时发生了什么,因为体制是由个人的行动改变的,而体制不可能自己改变自己。此外,历史决定论认为,体制改变人类行为的观点,不能说明当两个体制或社会冲突时发生了什么。波普尔争辩说,不仅体制的建立涉及个人的决定,而且最佳体制之起作用也总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有关个人。他将体制类比于堡垒,堡垒必须由人来设计和占领。这是对的。然而,一旦体制或堡垒建立了起来,它们必然对处于它们之内和之外的人产生影响。因此,认为在体制与个人行动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是合理的:体制可引起个人的行动,而个人的行动反过来又改变体制,体制的改变又反过来引起个人的行动。
此外,波普尔的世界3在这里也引起了问题。他声称,世界3是于个人的决定,不能还原为人类的行动,一旦建立,对人类思维有强制性后果。波普尔关于世界3自主性的论证似乎同样可应用于社会世界,也许可称之为“世界4”,尤其是因为波普尔强调个人面临的境况以及个人行动在这些境况中非意向的后果。承认社会体制或境况对个人行动的影响同他的关于下向因果作用的论证是一致的。[5]因此,波普尔的还原个体论与他的世界3学说不一致,也与他对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反还原论不一致:他反对将化学还原为物理学,将精神状态还原为物理状态。当社会整体论的支持者否认个人行动对社会体制的上向因果作用将个人仅看作实现某一社会集团、种族或阶级使命的工具而忽视个人利益时,他们是错误的。然而,用还原个体论来反对社会整体论就太强了。毕竟,社会要比个人的总和多点东西。个体论和整体论都各执一端;它们都掌握部分真理,但不是全部真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永久的张力。当它们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采取务实的态度来按具体案例具体解决冲突。波普尔在社会世界上的还原论与他在自然世界上的反还原论也许可以用他重视人类精神的创造性来说明。一个物质客体很难超越下向作用,但人类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即使如此,也不应忽视,包括个人创造性在内的个人行动受他们社会文化情景的制约。因此,波普尔的社会理论也许最好修改为:同意社会体制在许多情况下不能还原为个人行动,承认社会体制和世界3对说明人类社会是基本的。因而可以争辩说,社会体制的改变一般是非决定论的,个人行动可影响这种改变:它们之间有某种相互作用。
权力主义
波普尔发现历史决定论中有权力主义的倾向。如果恰如历史决定论者断言的那样,理想社会是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的必然结果,就要根据这些规律事先设计理想社会计划。为了实现这些计划,利用知识和权力来迫使不愿意接受计划的人参加进来,就是合理的和合乎伦理的,这里权力主义是用来达到理想社会这一崇高目的的手段。然而这种权力主义很容易窒息的创造力和批判力。
对波普尔来说,社会可看作是解决问题的组织。在他关于开放社会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如何应用他的猜测和反驳的科学方法于社会领域。在社会中,与在科学中一样,最佳的猜测可以来自任何地方,不只是来自上面。所以,信息不仅从上面流向下面,而是也从下面流向上面。这就要求在所有层次进行自由讨论和在所有成员中进行自由交流。这样,某种形式的自由和就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波普尔的开放社会中,科学共同体特有的自由讨论应该是社会共同体的模型。虽然我认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规范图景优于封闭社会,但存在如下的问题。
首先,不知道有关信息如何能够传播到经济和教育上落后的国家中的所有成员。最重要的是,社会成员要有时间来倾听所提供给他们的信息,并且有能力来理解这些信息。如果维持生存、养家活口占据了他们几乎所有时间,或他们是或几乎是文盲,他们就很难参与自由讨论和作出理性批判或决定。当某些西方人急于输出他们的到发展中国家时,他们忘掉了这一简单的真理。他们在哪里这样做,那里就出现混乱,而没有可言。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穷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自由受限制或受剥削,也总是难以分享信息和自由讨论。
有人反驳说,在一个大的社会中,种种不同的社会、民族和文化集团有着不同甚至迥异的各自目的,不可能按照波普尔建议的那样完全靠争论理性地达到一致。这不完全对。波普尔的错误在于过分相信人类理性。人类理性同科学和权威一样,有它的局限。不同社会、民族和文化集团之间的不一致或矛盾应该而且可能通过争论后的对话、磋商和协商来解决。争论是必要的,但是不够的。需要的是妥协。每一个集团应该在任何时候准备与对方妥协。我同意丘吉尔所说的,是最糟中的最好的。主义比权力主义要好,但它不是人间天堂。
经济决定论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波普尔对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批评。对波普尔来说,经济决定论是“主张,社会的经济组织,人们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组织,是一切社会体制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2,v.2,p.106]在波普尔看来,用经济决定论来补充历史决定论。结果是:“所有的、所有的法律和机构以及所有的斗争只是阶级之间的经济或物质实在和关系在和观念世界中的表现,它们决不可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是软弱无力的。”[2,v.2,pp.119]
我们可以发现著作中的某些段落也许看起来像是经济决定论。如:“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多或少得到急剧的改造。”[7,p.9]但其他段落不能证明波普尔的指责:“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将无产阶级提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将利用它上的无上权威从资产阶级夺取资本。”[8,p.481]
波普尔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论据是,经济决定论认为历史由仅基于经济因素的阶级结构决定,依赖于对人类行动动机的错误观念,而非经济因素同经济因素或多或少同样重要。
在我看来,经济决定论的概念并没有很好地限定。如果它指在人类历史中仅是经济因素重要,而其他不重要,人类历史的一切变化只能用经济变化来说明,这种经济决定论就过分简单化,而站着住脚。然而,及其亲密战友恩格斯并不是这种经济决定论者。恩格斯有一次写道:“按照唯物史观,历史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和我的主张从未超越这一点。年轻人有时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我对此有部分责任。我们在反对对手时不得不强调主要原则,我们并不总有时间、地方和机会来赋予相互作用中的其他因素以应有的地位。”[9,p.493]
所有前主义的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忽视了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的特殊作用。特殊作用在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形成社会基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然而,这并不排斥其他因素的作用。波普尔对理论的描绘是简单化的。更清楚地看到了其他学者看不到的东西,即经济因素的特殊作用,正是的功绩,而不是他的错误。这个星球上当代人对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有着活生生的经验。相反,以后的一些主要的主义者,却过分地强调了因素。当西方家坚持要将他们的制度加于发展中国家,而不关心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时,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
所有基于实践的挫折而摒斥的理论为胡说或伪科学的试图,都忽视了在我们关于人类和社会的思维重新定向中的重要作用。和主义者引入的,作为对现代社会社会和经济动力学更为精致的理解的基础,是永远具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karl popper,1978,unending quest: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fontana.
[2] karl popper,1952,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3] karl popper,1957,the poverty of historici.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4] karl marx,1969,"thesen uber feuerbach",in marx engels werke,band 3,p.535,berlin:dietz verlag.
[5] karl popper and john eccles,1977,the self and its brain,pp.14-21,berlin:springe.
[6] karl marx,1972,capital,in marx engels werke,band 23,berlin:dietz verlag.
[7] karl marx,1972,"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economies",in marx engels werke,band 13,berlin:dietz verlag.
[8]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1972,manifesto of ,in marx engels werke,band 4,berlin:dietz verlag.
[9] friedrich engels,1967,"a letter to joseph block,september21,1890",in marx engels werke,band 37.
玻尔“概念构架”的扩展与“两种文化”的统一_其他哲学论文 第八篇
摘 要:玻尔注意到物理学与其他知识乃至所有人类知识的不同方面存在着对立现象,他主张通过对认识“概念构架”的扩展来消除这种不良现象,其中的核心思想是“互补观”。然而,这并不能尽然消除“两种文化”现象。
关键词:量子论;互补性;知识统一性
abstract: nields henrik david bohr has noticed that there exists a phenomenon of split plus antithesis between phys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including all branches of human knowledge in terms of different aspects. he holds that such a phenomenon could be eliminated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nded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the core of his idea is of the mutually complementary. we cannot, however, remove “two cultures” with such an approach in a satisfactory way.
keywords: quantum theory; mutually complementary;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一、“两种文化” 及互补观的普遍性
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大部类,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www.meiword.com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得到了飞速发展,学科门类日益增多,人类知识迅速朝着分化的方向发展着。相应地,各学科知识之间也日见隔膜。至十九世纪下半叶,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对立已经相当严重,这一状况在二十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为科学史学之父萨顿所关注,他从此将自己的一生主要工作目标定为要令“科学人性化”,即要使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到50年代,英国的c.p.斯诺则明确地指认了“两种文化”的对立现象,指出这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并大声疾呼两种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必须握手言和,共同推进人类的文化事业,推进社会的进步。
如何认识和处理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早已成为人类长期思索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今,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对其解决也更富有挑战性。
对于两种文化的对立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后果,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作为对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极度关切的人,玻尔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他充分认识解决两种文化问题的难度,同时又将之视为人类知识达到一次新的统一的良好机会。玻尔指出:“在我们的年代,随着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日益专门化,这一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文学家们和科学家们对人类问题采取着明显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由这些处理方式所引起的广泛的混乱,人们从各方面表示了关怀,而且,与此有关,人们甚至谈论着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裂痕。”[1](p243) 但是,他提醒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很多知识领域都在迅速发展的时代,这种情形就如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样,尽管由于从中世纪世界观中解脱出来极为困难,所以人们把当时的科学进步视为“科学革命”,其成果曾被视为十分巨大,但如今看来只不过是普通文化背景的一部分而已。“在本世纪中,各门科学的巨大进步不但大大推动了技术和医学的前进,而且同时也在关于我们作为自然观察者的地位问题上给了我们出人意料的教益;谈到自然界,我们自己也是它的一部分呢!这种发展绝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和物理科学的,它只带来了对于我们对待普通人类问题的态度很为重要的消息;正如我要试图指明的,这种消息给知识的统一性这一古老问题提供了新的远景。”[1] (p243)
追求知识的统一性是人类的不懈努力,而知识统一的新远景玻尔认为有赖于互补观念的确立。“由于机械自然观对哲学思维的影响,人们有时感到在互补性概念中有一种和科学描述的客观性不相容的关于主观观察者的论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互补性概念绝不包括和科学精神不相容的任何神秘主义,它标示了描述与概括原子物理学中的经验的逻辑基础。”[1] (p208)
玻尔指出:“利用同一种实验装置,我们可以得到对应于各种个体量子过程的不同纪录;关于这些个体量子过程的出现,我们只能做出统计的说明。同样,我们必须准备发现:用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实验装置得到的资料,可以显示没有前例的对立性,从而初看起来这些资料甚至显得是矛盾的。” [1](p243)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对于微粒,在不同视角下考察所取得的结论各异,这些结论却都是正确的,都是我们要达到对微观粒子完整的把握所必须的。
对于微观粒子的考察表明:在同一实验装置中,一般会出现和不同的个体过程相对应的观察结果。对此,“我们不能寻求一种习见意义上的物理解释,我们在一个新的经验领域中所能要求的,只是消除任何表观上的矛盾而已。无论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原子现象表现得多么矛盾,其中每一个现象却都是明确定义了的,而且所有这些现象的总体就包罗了有关客体的一切可定义的知识;在这种意义上,这些现象必须被认定是互补的。量子力学表述形式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概括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得到的观察结果;这些实验条件是用简单的物理概念来描述的。这种表述形式,恰恰给出了一个很大经验领域的这样一种包举无遗的互补说明。”并且“这种表述形式必须认为是经典物理学的一种合理的推广。” [1](p208) 很明显,玻尔认为从量子力学中归结出的互补原理完全可加以推广使用。
玻尔的互补原理源于量子物理,是从波粒二象性理论概括、引申而来。因此,从严格的物理学含义上说,戈革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两个互补的图像(例如微观客体的波动图像和粒子图像)根本不可能结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图像”,“当我们使用其中的一类时,另一类就不出现或不成立,从而二者并不会在实际上处于正面的冲突的状态。”两者互斥图像之“互补”的含义,仅仅是二者对于完备地描述微观对象的不可偏废性,“必须平等地承认它们并结合不同条件而适当地使用它们,才能把事情作到完备的地步。”[2] 根据张建军先生的研究结果,可以依据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矛盾法则对以上事实作如下诠释:微观客体本身都拥有波动性与粒子性相反相成的客观矛盾结构,二者“不断‘斗争’着或相互作用着”。玻尔明确指出:“测量仪器作用过程的说明本身就意味着,作用量子所蕴涵的这些仪器和原子客体之间的任何相互作用,都是不可分割地存在于现象中的。”由于观测仪器与微观客体的相互作用对于观察的不可忽视性,使得不同的观测实验带来微观客体的波动性与粒子性在与观测仪器相互作用过程中,矛盾双方主次地位随之发生变化:当波动性占主导地位时,其宏观度量表现为波动图景,而当粒子性占主导地位时,其宏观度量表现为粒子图景。张建军先生指出,玻尔的互补原理所谈论的直接对象并非物理客体及其客观结构,而是物理学的理解方式、描述方式、经验、图像或概念等,属于“认知规范”范畴。因此,宏观上波动性和粒子性虽然“不可能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图像”,但这并不说明微观客体自身不存在客观矛盾,而只说明由于人类受限于自身无法摆脱的宏观性,就无法用直观模型或图像去描述微观实在的辩证结构,只能而且必须通过不同侧面认识的综合,间接地予以整体性把握。这样,互补原理所体现的认知方式,就成为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矛盾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3](p95—99)
实际上,在玻尔看来,互补的思想观念是正确思维的普遍要求,因为严格说来,任何概念的知觉和直接应用都有一个排斥的关系存在,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对之加以互补性把握。例如,关于生命现象的整体性研究和还原性研究、心理学中的思想和感觉、人类社会的公正立场和仁慈立场、一切成功艺术共有的严肃性和幽默性等,都是互斥互补的。显而易见,人类认识的互斥互补性是一个普遍的认识原则,它由物理学概括出来但又不受限于其特殊含义,它超越了物理学而具有哲学和认识论的意义。
二、“概念构架”扩展:人类知识是统一的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文化”现象?玻尔认为这主要是我们认识事物,或具体地说是我们理解和把握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所赖以的“概念构架”的狭隘性造成的,只要我们扩展“概念构架”,开阔视野,就会发现人类的知识实际上是统一的。这无疑也就是消除“两种文化”的可行途径。
玻尔指出“一切知识都是在一种用来说明先前所有的经验的观念构架中表现出来的,而且任何的这种构架在概括新经验方面都可能是过于狭隘的。” [1](p181) 这一断言是符合认知科学结论的。现代认知科学已经清楚地表明,人类的认知是在一定的认识背景或说框架下进行的,而认知的结果——知识获得所依赖的背景框架亦即玻尔所谓的概念构架,其所以形成的基础自然是先前已有的经验。用这样的概念构架去认知新事物,确实难免产生过于狭隘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皮亚杰在通过对人类认识发生、发展的考察与研究后得出结论说,认识主体所特有的两种主要机能是组织和适应,而主体的每一行为活动都是组成或建构的,因此就具有一定的结构,其动态方面就是适应,而适应本身则是同化和协调相平衡的过程。当外部事物作用于主体时,主体便加以选择并将新的客体纳入已经存在的图式之中,这一过程称为“同化”;如果新的作用不能完全为已有图式所包含,主体就会改造图式以适应新客体,这种使主体图式符合客体的过程就是“协调”。可见,为了达到对客体的认识,主体必然根据自身的智力和心理因素观念地作用于它们,从而改变它们:混合、联系、分组、打乱秩序和重新建构。在认识过程中,这种同化和协调作用贯穿于始终,直至达到对客体的把握。玻尔所说的用已有构架去认识新经验,这种构架必然会显得过于狭窄,这实际上也就是皮亚杰所指出的新客体与已有图式不相一致,无法以同化方式认知,故而必须改造旧图式来适应新客体,以协调方式达到认知、把握新事物的目的。就对旧图式的改造以使知识统一起来而言,玻尔认定其主要方式是对“概念构架”加以扩展。
玻尔还进一步指出:“事实上,观念构架的扩张不但适于用来在有关的知识分支中保持秩序,而且也显示了我们在表面看来相去很远的知识领域中。” [1](p181)“在量子物理学的互补描述中,我们遇到一种更进一步的自相协调的推广;这种推广可以远远超出物理科学范围,直至可以用于对知识统一性的寻求。” [1](p189) 由此,他推论并举出了种种实例。如科学与艺术、正义与仁慈、不同的民族文化,等等。他说:“不论是在科学中、在哲学中还是在艺术中,一切可能对人类有帮助的经验,必须能够用人类的表达方式来加以传达,而且,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将处理知识统一性的问题。因此,面对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发展,我们就可以寻索一切文明中生根于共同人类状况中的那些特色。尤其是,我们认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本身,就显示着多样化的、往往是互斥的一些方面。” [1](p247) 但是,“在科学中,我们所遇到的是论证经验并发展概念来概括这些经验的系统协作,其作法就如同把石头搬来并垒成一个建筑一样;而在艺术中,我们所遇到的却是更加直觉地唤起情感的个人努力,这种情感使我们想到自己的处境的整体。然而,在互补观下,科学与艺术两种知识也是具有统一性的。” [1](p196)
在看待正义与仁慈、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时,玻尔告诫说:“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地表现在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那种哲学提醒我们,在生存大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1](p247) 这其实就是说,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双方既具有对立性,又有同一性。正如任何矛盾双方一样,它们虽然对立,但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一言以蔽之,在互补观之下,它们实质上是统一的,关键是要扩展我们“看” 问题的概念构架。
由此衍生出的一个问题是,概念构架的扩展是否会造成其客观性的丧失而变成纯粹主观任意性的东西?玻尔对此的回答是:当谈到一种观念构架时,我们不过是指经验之间的关系的无歧义逻辑表现。虽然概念构架难免夹带一些偏见, “但是,有决定意义的一点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的观念构架的适当扩展,都不蕴涵对于观察主体的任何引用。否则,就会阻止经验的无歧义传达。在相对论性的论证中,这种客观性是通过适当照顾现象对观察者参照系的依赖性来加以保证的;而在互补描述中,则通过适当注意基本物理概念之明确应用所要求的条件来避免全部的主观性。” [1](p181) 正是由于客观性必须保持,因此扩展概念构架并不会导致主观性。
“原子世界中的研究怎样提供了新的机会来寻索奥斯特所谈到的自然界的和谐性,这种和谐性我们或许宁愿称之为人类知识的统一性。确确实实,只有意识到这种和谐性或统一性,才能帮助我们对我们的地位保持一种均衡的态度,并避免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在几乎每一人类兴趣领域中可能如此容易地引起的那种混乱。” [1](p255) 而在不同生活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人类文化,在所建立的传统和社会类型方面表现出了如此强烈的差异性,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并可以把这些文化看成是互补的。……在我们的时代,当增长着的知识和能力将人类的命运空前密切地联系起来之际,科学中的国际协作要求日益广泛,日益迫切,这就要靠我们对于人类知识的普遍理解来推进。总的说来,“力求做到和谐地概括我们的越来越广泛的处境,承认任何经验都不能不用一种逻辑构架来加以定义,并承认任何外观上的不和谐都只能通过概念构架的适当扩充来加以消除。”这也就是解决文化不同方面的对立,达到知识统一性所应持有的态度。[1](p211)玻尔指出,相对论观点肯定也有助于促成对待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种更加客观的态度;事实上,相对论的世界图景的统一性,精确地蕴涵了一种可能性:任何一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自己的观念构架中预见到任何另一观察者在他自己的构架中如何描述经验。然而,我们在对待其他民族文化时,总是以自身根深蒂固的传统为背景和基础,这就难以做到无偏见性,或说难以做到中立,这也就客观地决定了我们不能对各种不同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更不能对之轻率地加以褒贬。
当研究和我们自身文化有所不同的其他民族文化时,我们需要处理一种特殊的观察问题; 在原子物理学中,对于用不同实验装置得到的,而且只能用互斥的概念来具体想象的那些经验,我们用互补性来表征它们之间的关系;按照颇为相似的办法,我们可以正确地说明不同的人类文化是彼此互补的。每一种文化都代表传统习惯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平衡,利用这种平衡,人类生活的潜在能力在一种特定的方式下表露出来,以使我们认识到它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多样性。众多实例证明,不同民族或社会阶层之间的接触可以日渐导致传统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又导致全新文化的产生。“事实上,通过关于文化发展史的一种与日俱增的知识而对逐渐消除偏见有所贡献,这或许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最大希望;逐渐消除偏见,这正是所有科学的共同目的。” [1](p136)
玻尔认为,互补思想或说互补原理是具有广泛性的,它不局限于物理学,而可以外推到人类几乎所有的领域。由互补性得来的较宽广的构架,绝不会导致任何对于因果性这一理想的随意放弃,它直接体现着我们在说明物质基本属性方面所处的地位,这些属性是经典物理描述的前提,而它们又超出经典物理描述范围之外。历史现实一再证明,我们“有必要引用互补性思想来提供一种足够宽广的构架,以容纳那些不能概括在单独一个图景中的基本自然规律的说明。事实上,在明确规定的实验条件下得出的、并且是适当应用基本物理概念表示出来的那种资料,就其全部来说就完备无遗地概括了可以用普通语言来传达的关于原子客体的一切知识。” [1](p243) 互补思想概念的树立,认知构架的扩展,在玻尔看来已从根本上说明了包括科学和人文在内的人类知识的统一性。换言之,在此,两种文化现象已被有效地消除了。
三、 作为认知前提的“概念构架”与“认知图式”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表明,认识不能没有作为对象的客体,也离不开主体自身。客体的结构和特性制约着主体的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也制约着认识的活动和水平。主体素质包括主体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其中,既有先天固有的成分,又有通过实践和学习逐步养成和内化而获得的成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主体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都制约着认识的发生、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像,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像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4](p76) 就主体的精神素质而言,它是人的社会性的集中表现,它深刻地影响着认识的全过程,成为不同主体对同一事物形成不同认识的决定性条件。鲁迅曾经揭示: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的是“易”,道学家看见的是“淫”,才子看见的是缠绵,革命家看见的是排满,荒诞家看见的是宫廷秘史。面对同一事物,各人有各人的认识,有时差异很大,甚至对立,这是由主体不同的精神素质所决定的。这种素质还可分为认知图式和非理性因素两大部分。前者是思维方式、科学知识、价值观念等方面凝结而成的统一体,它们共同制约主体反映客体的全过程,具体体现为:
第一,认知图式制约着人们每一具体认识过程的目标选择。
第二,主体按照自己的认知图式整理来自客体的信息。主体认知图式中具有的观念、知识、经验等因素所形成的种种较固定的联系,决定着主体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整理客体信息。例如,既可以在日常生活经验层次上,也可以在某一具体科学层次上,还可以在哲学观念层次上去整理信息,把握客体。
第三,主体按照其认知图式对客体做出解释。不同主体原有认知图式的思维背景不一样,对客体的理解和解释也会出现差异。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以上观点,已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等为代表的现代认知科学所证明。从此我们可以得知,人们对于两种文化及其关系的不同看法以及不同的解决方式,实际上是由于其在相应的过程中所运用的认识图式不同所导致。而反过来,无疑也就可以说,若要使人们改变对原来看上去差异较大甚至对立的观点,就要改变其现有的认知图式,认知图式即相当于玻尔所谓的“概念构架”。因此,玻尔主张扩大“概念构架” ,并以其互补原理来重新考察、认识人类知识的各部分,就再也不会将之视为相互对立的,而是人类知识的整体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可截然割裂开来。从此意义上说,玻尔是十分正确的。
此外,还应指出,玻尔的“概念构架”与皮亚杰的“认知图式”虽然都是指一种认知的背景和基础。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内涵上看,前者指的是要注意之所以对事物尤其是对同一事物的观测得到不同的结论,是因为观察环境(实验环境)不同,它们实际上都属于事物所具有的属性,人们觉得结论是相互矛盾的,是因为视界不够宽广,只要扩大了“概念构架”,就能容纳这些不同的观点,达到全面把握事物的目的。这时实际上我们也就达到了视界的融合。而皮亚杰的“认知图式”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视界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构成要素。“认知图式”是要解决人们的认知何以可能的问题。当然,由于它强调其中内含了诸多要素:心理、逻辑、社会等因素(认知、审美、道德或说真、善、美因素),所以以这种“认知图式”去认识事物,其片面性就会少得多,就不会极端地认为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是截然对立的。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皮亚杰由于未能充分考虑社会实践等诸多要素,所以,以其“认知图式”去认知也就不能达到对问题的尽然解决。尽管如此,他强调认知图式中所包含要素的全面性,其中包括科学认知、道德和审美,乃至社会实践要素等是合理的。若以皮亚杰的认知图式去考察人类知识的同一性,就必然要求从各部分不同的知识之间的共性着眼。而玻尔以互补思想为出发点来求得两种文化统一的做法,更多的是要求人们要有包容心,这就多少有点类似于罗蒂以所谓的“亲和”、“友善”姿态去包容不同观点和意见,依靠个人的“德性”去消除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而实际上这样做却未曾真正解决问题,至少可以说未尽然解决问题,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对立状况仍然真实地存在着,关于这一点以下将作进一步的说明。
四、“概念构架”扩展:必要但不充分
玻尔认为,只要扩展“概念构架”,人类的知识就是统一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两种文化对立的问题。然而, “概念构架”的扩展可能会导致“认知图式”过于宽泛,进而会产生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无法界定的大问题。换言之,在扩展了的“概念构架”下,就无法判断科学文化之所以是科学文化而非人文文化。反之,亦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别已被人为消除,因而可能产生“此亦彼也,彼亦此也”的后果。这正如混沌专家斯图尔特(ian stewart)所比喻的:我们可以无限扩展“象”的定义而把一切动物都说成是“象”,比如说猪是短鼻子无牙象,鸡是尖嘴巴有羽象。若真要这样去做的话,大象与鸡、猪之间必难区分。玻尔主张扩展“概念构架”,也就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倾向和危险。而对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或抹杀,无疑也就消解了这两种文化的对立问题。然而,问题的消解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区别,乃至两者之间的对立依然客观地存在着。
要想解决这种冲突与对立,必须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下,或说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在承认两者之间的差别与对立的同时,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并着力说明正是这种同一性,使得两种文化实质上并非是水火不相容,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的人类文明之花。显然,要真正达到不同部分知识的协调、融合,找出其间的统一性(共同因素),或各自的特性,以及功能不一但互补(且为达到共同目标皆不可缺少)是关键。
玻尔的互补观,实际上注意到了不同知识的不同语境性,可将视之在“不同视角” 即形式逻辑中所说的非“三同一”下对事物的判断,各断言之间因而是不会构成冲突的,若要说它们之间有矛盾也不属于形式逻辑矛盾,而是辩证矛盾,因而都是可以成立的,对于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也应持如是观。
然而,如此也未能尽然解决“两种文化”的现象。因为玻尔在此所能达到的只是一种“视界的融合”,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增进了两种文化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和解,因此扩展“概念构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充分,人们毕竟还是不会因为 “概念构架”的扩展而达到从不同视角去看待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目的。显然,两种文化的视界融合并不等于其内在的统一,仅仅宣布两种文化是不同语境下的知识,都是人类整体知识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未解决两者之间真实存在的冲突。因此,寻找一种可以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加以比较的共同标准仍然是必要的,只有通过真正切实的比较,再指出其各有千秋的特性和作用,才能说明两种文化必须并确实是互补的。又通过指出它们之间存在的统一性,可以有力地说明它们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人为造成的、非法的。要真正达到不同部分知识的协调、融合,找出其间的统一性(共同因素),或各自的特性,以及功能不一但却具互补性当是关键。[5]
k. e.鲍尔登指出,只要整个物理学界、生物学界、还有我们自己和整个社会都有较充分的认识,我们就能把演变的进程向着改善的生活、建立更幸福的人类世界推进,以摆脱重重灾祸的苦难。但是要使这一希望得以实现,科学界本身也必须向前发展。它需要对所肩负的使命和自己的伦理标准有新的认识;它需要研究出一套符合认识规律的方,并且要认识到人类知识的统一性,以便把自然科学各学科与人文学科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填平;它需要创立一门可称为“规范科学”的学科,以便认真研究和评价人类本身的价值;它需要更深刻地认识到,科学作为世界性的活动是超越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但又要保留某一民族、某种文化的特色。把它看作人类进化的关键所在。 我认为这些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它应该成为我们追求人类知识同一性的必经之路。
[参 考 文 献]
[1] 尼尔斯•玻尔哲学文选[m].:商务印书馆,1999.
[2] 戈革. 尼尔斯•玻尔和他的互补原理[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5).
[3] 张建军. 如何理解微观客体波粒二象性的辩证性质[a].矛盾与悖论研究[m]香港:黄河文化出版社,1992.
[4] 恩格斯. 反杜林论[a].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出版社,1972.
[5] 笔者曾就此进行过一定的探索,请参见黄瑞雄.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何以可能[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6);哲学原理(人大复印资料),1999(3).
[6]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商务印书馆,1981.
联结主义、排除主义和思想的构成性_其他哲学论文 第九篇
在认知科学中,经典的符号主义模型和新近兴起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模型在认知结构上的争论目前愈演愈烈。按照经典主义,认知是在符号表达式(例如语言表达式)上进行的受规则制约的变换,而对这些符号表达式则能提供明确的语义解释。但按照联结主义,根本的认知机制并不是符号的,相反,它们可以在一种类似神经网络的结构上得到说明;对于这个结构的单一的基本要素,则不能提供明确的语义解释。它们之间的区别可以称为符号与亚符号(symbolic-subsymbolic)之别。
在一系列争论中,关于思想的构成性(the compositionality of thought)的争论尤具代表性。所谓思想的构成性,主要是指思想之间由于其内在的语义关联,而系统地相互联系,以及人的思想在合理性原则和逻辑推理原则的支配下,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经典主义由于假设思想的构成要素具有似语言的结构,因而能比较容易地解释构成性问题。一些经典主义者认为,联结主义模型在根本上不能说明这一问题,所以它们不适合作为认知模型。另一方面,一些联结主义者则论证说,经典认知科学承诺了常识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但联结主义的探讨表明,这些原则是假的,所以,正是经典主义在人类认知的模拟上误入歧途。联结主义把这个论证称为对经典主义的排除主义(eliminativi)论证。本文将一些联结主义者对经典主义的排除主义论证,并表明思想的构成性问题对于这个论证至少是中立的。
一、联结主义和排除主义
简单地说,排除主义是这样一种主张:科学的发展将表明,在常识或对世界的日常论述(甚至于过去的科学论述)中,所采纳的某个范畴的实体、过程和性质并不存在,这些东西最终应从严密科学中被排除掉(p.feyerabend 1963,r.rorty 1970,p.churchland 1981)。WwW.meiword.com排除论者乐于引证的典型例子是燃素和热质。随着神经科学的兴起,一些当代的排除论者认为,日常谈论的精神状态甚至也是排除的对象,成熟的认知科学不应该授引精神状态这样的概念来说明人的认知活动和认知能力。因而排除主义的关键论证是要表明,设定了某些实体或过程的一个理论应被一个更好的理论拒斥或取代,如果后者比前者提供了更精确的预言和更好的说明。当然,仅仅是新理论的说明的合适性和预言的精确性并不足以表明旧理论所设定的实体或过程不存在。更严格的论证需要表明,旧理论的本体论完全是假的,对于设定来说明现象的那些实体,新理论提供了更精确的说明。如果是这样,从旧理论向新理论的转变可以称为本体论上激烈的转变。于是,对命题态度心理学的排除主义论证大致如下:
(p1)命题态度心理学是真的,当且仅当关于心智的最好科学为之提供了基础;
(p2)这门科学并未为命题态度的概念提供基础;因此
(c)命题态度的概念应从关于大脑和认知的成熟科学中被除除掉。
联结主义者对经典主义的排除主义论证立足于这一点:常识心理学承诺了命题模块性论点。以下我首先将考察这一论点,接着这个排除主义论证的基本思路。在接下来的两节中,通过经典主义和联结主义对于思想构成性问题的处理,我表明这个排除主义的论证并不是决定性的,经典模型和联结主义模型的关系仍是一个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经验探究的问题。
1.常识心理学和命题模块性论点
常识心理学的捍卫者认为精神状态是语义上可评价的、有因果力的离散状态(j.fodor 1987)。在提炼排除主义和联结主义的关系时,常识心理学的关键信条是:命题态度是功能上离散的、语义上可解释的状态,这些状态在其他命题态度的产生中,以及根本上在行为的产生中起着因果作用。这里,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点:常识心理学认为命题态度具有语义性质,因为正是由于一个信念具有特定的语义内容,它才具有特定的原因或效果。语义性质的独特性成为功能离散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命题态度的功能离散性是针对它们的组织而言。由于这种组织的离散性,可以合理地说一个人已获得或失去了一个单一的信念,或者,一个人可以一次把一个信念增添到他的资源库中去。
在心理学文献中不乏有采纳命题模块性论点的信念或记忆模型。在传统认知心理学中,一个著名的模型是由a.collins和m.quillian (1972)发展起来的记忆的语义网络模型。这种记忆组织模型为每个记忆设置了一个不同的语句或准语句结构。按照这些模型,记忆可以被看作一系列准语句结构,每个结构对应着一个分离的信念。如果信念或记忆贮存是以这种方式被组织的,那么确定导致言语行为的一个信念状态就很容易,它不过是结构化的记忆网络中的一个分离的语句或公式。这种模型明确解释了记忆修改和从语义记忆中回收信息的方法。
然而近年来,一些理论家对这种高度模块化的模型产生了怀疑。一个主要的理由是,语义网络模型不能说明我们迅速有效地在记忆中确定相关信息的能力,与此相关的是对非归纳推理模型的日益关注。因为越来越清楚的是,语言使用和语言理解要求大量的非归纳推理(r.schank,1987;t.winograd,1981)。在达到对一个单一的日常话语的解释时,必须同时运用与话语的题材、说话者的意图、交流的场景等等有关的信息,所需要的大量信息并不是从听话者的信念内容中推出来的。为了说明我们解释一个话语的能力,相关的认识模型必须假设一种在非归纳推理中促动记忆之有效使用的记忆结构。m.minsky则充分表明,把专门知识和一般推理规则完全分离开来的策略太极端,我们需要把专门的知识片断与如何使用它们的特定规则联系起来。进一步,思想的机制要被分解为许多相互作用的单元;但是,这些单元没有一个本身“具有意义”,因而没有一个能被等同于个别的命题态度;意义或内容只能从“巨大的结构网络”中突现出来(m.minsky 1981a,1981b)。这自然得出了一个与模块性论点不相符合的结论:认知系统中没有哪个自然的部分能与“明确的”或言语上可表达的信念相联系。
相比较,使用分布式表达的联结主义模型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些认知事实,尤其是说明不受明确的“硬规则”支配的认知现象。这为排除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思想契机。他们的逻辑思路是:常识心理学承诺了命题模块性论点,如果联结主义模型表明模块性论点是假的,而且对一些认知现象提供了更合适的说明,那么也就表明了常识心理学是假的。
2.对排除主义的联结主义论证
联结主义是在最近十年突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认识模拟型式。受神经结构的启发,联结主义模型由大量格外简单的相互作用单元组成的网络构成。网络的单元之间能够相互发送激活或抑制,激活值受动力学方程支配。通过改变网络之间的联结权,可以改变网络联结的学习规则。一般来说,有两种类型的联结主义网络。局域式网络(localist networks)把每项信息存贮在网络的一个单一单元中,而在分布式网络(distributed networks)中,每项信息则在许多不同的单元上同时得到表达,信息被迭加存贮。
这种结构支持着一种与经典认知模型所采纳的表达和计算截然不同的表达和计算。经典模型的操作最好被描述为“符号处理”。在这种模型中,信息一般是被存贮在与执行计算操作的结构相分离的不同位置。因此经典模型的信息处理是由离散的符号标志构成的;按照易为该模型识别的方式被编码的规则或指令,那些符号被重新定位、复制和改组。在经典模型中,可以为每个符号表达式提供一个语义解释。然而,相比较,联结主义模型一般并不使用离散的符号实体。在这种模型中,表达是用迭加的、分布的方式进行的。“每个实体由分布在许多计算元素上的一个激活模式来表达,而每个计算元素在表达许多不同的实体时又都被涉及到”(rumelhart and mcclelland,1986,p.77)。这样便产生了联结主义模型和经典模型的一个显著差别:在联结主义模型中,存贮信息的结构和处理信息的结构的区分实际上并不存在;信息就存贮在个别单元之间的联结权中,而在处理中,这些联结权也充当了中心的要素。因此,制约着计算过程的自主的控制结构的概念在联结主义结构中似乎没有地位。采用分布式表达的联结主义系统的个别单元的活动无须是语义上可评价的。相反,得到一个语义解释的是某个单元子集的组合活动。结果是,一项特定的信息被认为在网络中得到明确表达,当且仅当在某个特定的单元子集上,一个特定的激活模式在回答这些单元的输入时被产生。但明确表达只是采用分布式表达的联结主义系统的暂时特点。如果网络的输入发生变化,那么构成它的处理单元的激活值也发生变化,结果被明确表达的信息也随之而变。因此,这种系统不能以在构成单元上产生的激活模式的形式长期编码信息,长期的信息编码是由隐含表达实现的。分布式表达决定了联结主义系统的信息处理的整体论。
正是这种信息整体论成为排除主义者论证的起点。w.ramsey等人构造了一个联结主义的记忆模型,此模型能够从事更传统的认知模型所从事的一些任务,但却显示了分布式编码的特点(w.ramsey,et,al.,1990)。这个模型的基本特点是:由于信息是以高度分布的方式进行编码,每个联结权体现了对于许多命题来说突出的信息,而关于任何特定命题的信息又分布在整个网络中,因此,系统缺乏那种可以在语义上解释为个别命题之表达的功能上离散的、可鉴定的子结构。从模型建造者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这种网络模拟了具有某些信念的人的认知行为。然而,在这个网络中,被常识心理学处理为自然种类的东西并没有被看作自然种类。由此他们推断说,“一些联结主义模型并不具有在某些认知情节、而不是在其他认知情节中起着因果作用的离散的、语义上可解释的状态,在这些模型中,不能合理地鉴定出与常识心理学的命题态度相等同的东西。如果能够证明这些模型对人的记忆和信念提供了最好的说明,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本体论上激烈的理论变化。这种变化将维护这一结论:命题态度像燃素和热量一样,并不存在”(w.ramsey,et.al.,p.37)。
这个排除主义的论证最终是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验研究。然而,一个直觉是值得维护的,那就是,常识心理学的理论构造在某种意义上不同燃素说或热素说设定的理论概念。当后者由于近代化学的兴起而被排除掉时,前者并不由于神经科学或联结主义的兴起而被轻易排除掉。根本的理由在于,首先,常识心理学的概念框架本身具有强大的说明和预言能力;其次,采纳了这一概念框架的经典认知科学获得了一定的成功。[①a]以下我将表明,常识心理学并没有像排除论者所设想的那样承诺命题模块性论点,完全可以使联结主义与常识心理学相调和。
3.常识心理学与层次-1的描述
经典认知理论几乎完全接受了常识心理学对如下原理的所谓“承诺”:(1)按照命题态度来心理状态;(2)命题模块性论点:(3)命题态度是因果地产生的内在状态。如果常识心理学承诺了这三个原则,那么它的确成为承诺了另一组相当不同的原则的联结主义的排除对象。因为不像经典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并不把认知过程处理为受形式规则支配的符号操作。因而它提出了符号探讨是否是对认知模拟的正确探讨的问题。联结主义模型似乎能够执行认知任务,而不利用明确的对符号串进行操作的规则。在认知结构问题上,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因而成为一对竞争的学说。这样,如果经典认知科学对常识心理学的辩护要求它认为常识心理学承诺了上述原理,如果联结主义能够表明那些原理根本上是错的,那么常识心理学便面临着被排除的潜在危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排除主义者热衷于把常识心理学处理成一个关于内在过程的理论。[②a]这大概是因为意向实在论者认为常识心理学状态是因果相联的状态,而排除主义者惯于按照基本的物理机制来设想因果相互作用。然而,不是作为一个内部处理理论、更合适地说,常识心理学是一个高层次的理论,它表征有机体对环境的知识和它们在环境中的行为方式。一个真的信念可以向我们传达关于环境的知识,成为环境状况的一个可靠的指示者(h.field,1978)。一个真的信念和一个合适愿望的组合可以导致成功的行为。常识心理学的这一本质特征使它处于marr所说的任务层次(层次-1)上(d.marr,1982)。这个描述层次旨在于说明一个有机体或系统处理什么信息和为什么处理这些信息。只有完成了层次-1的,才能问它怎样处理这些信息(层次-3的描述)。常识心理学不是直接按照系统的内部结构,而是按照它们与环境相联系的方式来表征这些系统。就科学的发展来说,对这种关系的说明像对内部结构和过程的说明一样重要。当我们能够区分系统和它们所操作的环境,部分地处理这些系统,好像它们不受环境影响时,我们往往对系统的那些旨在满足环境要求的活动更感兴趣。对于智能系统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智能系统的一个本质特征便是对环境的适应性。不理解一个系统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就不清楚要对哪些内部性质给予最充分的注意。所以,一个关于内部认知过程的理论必须补充一个关于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因此,常识心理学不是任何内部处理理论(无论是经典理论还是联结主义理论)的竞争对手。如果经典主义能够合理地处理信念的语义性质,那么联结主义似乎也有潜力这样做。为了明白这一点,让我们转到经典主义和联结主义的一个中心争论上来。
二、思想的构成性;经典主义的挑战
j.fodor和z.pylyshyn(1988)通过区分对认知理论的表达主义探讨和排除主义的探讨开始他们对联结主义的批评。表达主义者声称认知系统的内在状态是编码世界状态的表达状态或语义状态,排除主义者则试图取消表达这样的语义概念。在提出这一区分后,他们把联结主义置于表达主义的一边。因为联结主义者典型地为个别单元或单元的组合提供语义解释。然而,他们论证说,正是由于联结主义的语义解释的特点,联结主义系统不适合作为表达系统。他们的根本结论是:没有一个符号表达系统的资源,便不可能有模拟认知过程的合适的表达系统;只有一个具有结构化的符号表达的系统能够合适地模拟认在过程。
fodor和pylyshyn的论证立足于符号表达的语言特征,立足于fodor所说的思想语言假说--认知活动要求一种似语言的表达媒介(t.fodor,1975)。因为我们需要以此来说明思想的产生性、系统性和推理的连贯性。思想的产生性是指从一个无限的集合中理解和生成命题的能力。由于这个能力是通过使用有限资源获得的,所以便需要递归操作。思想的系统性来自于这个事实;理解或思考一个思想的能力与理解或思考其他思想的能力是内在联系的。例如,能够思想x爱y的任何人也能思想y爱x。推理的连贯性涉及到做出句法上和语义上合理的推理的能力。例如,一个人能够从x是一只棕熊推出x是一只熊。这三个特征要求精神表达必须是语义上结构化的实体,这意味着:
(i)表达必须具有构成要素;
(ii)表达必须有一个句法;
(iii)表达的语义性质必须是它的构成要素的语义性质和它的句法的函数;
(iv)对复杂表达的语义性质做出贡献的构成要素的语义性质及其句法必须可以于那些复杂表达来指定。
从这几个特点可以看出,一个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是一个具有逻辑形式的表达。fodor和pylyshyn的主要论证如下。首先让我们考虑具有局域式语义解释的联结主义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每个表达单元是原子的,只有一种方式使单元之间相互联结起来,即通过对偶的因果联系。因此,如果a&b和a是网络中的两个节点,从a&b到a的联结权可以这样确立起来,以致于激活a&b将导致a的激活。这可以看作一种推理,但是a的表达根本不是a&b的表达的一部分。任何两个节点都可以被联结起来以便有同样的推理模式,例如,节点a&b可以激活节点z。这样一来,这种联结显然本质上不是构成性的。这种推理必须对每个合取实例分离地建构进入,而不是由一个规则来指定,此规则利用变量来指定句法包含关系。因此他们推断说,局域式的联结主义系统缺乏必要的认知资源。
分布式系统又如何呢?在具有分布式表达的某些网络中,一个特定表达中的活动单元编码被表达的实体的特点或微观特点。p.olensky提出了在分布式系统中实行结构化表达的一种方式。就组合结构问题来说,例如,“咖啡杯”的一组特定特点可以分成三个子集:一个集合只应于杯子(如,瓷的弯曲表面),一个集合只应用于咖啡(如,棕色液体),一个集合应用于相互作用时的杯子和咖啡,如,与瓷器相接触的棕色液体。按照olensky的观点,咖啡和杯子这两个特点子集包含在咖啡杯的集合中,这就取得了构成性的性质(p.olensky 1987)。然而,fodor和pylyshyn认为,olensky的解决并不奏效,因为他不能把一个具有语义和句法构成要素的表达和一个按照微观特点来编码的概念区分开来。一个微观特点是对一个对象的表达的一部分。这样,在对[李杨爱这个女孩]的符号表达中,对[这个女孩]的表达与此命题的其余部分处于某一句法关系中,以致于不把此命题与[这个女孩爱李扬]混淆起来。但对分布式表达就不是这样了。例如,对[李扬爱这个女孩]这个命题的一个最小的分布式表达可以由一个网络来实现,该网络的单元对应于[李扬]、[爱]、[这位女孩]这样一些概念;激活这三个单元便对此命题提供了一个分布式表达。然而,这个表达将不可区分于对[这位女孩爱李扬]的表达。继续对关系添加单元将是无助的,因为没有直接了当地的办法抓住这一事实:这个主体正是李扬,而不是这位女孩。这些单元是在共同发生的关系中被约束在一起,但没有句法所提供的结构。所以分布式网络也不能处理构成性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在复杂符号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经典区分不能被特点集及其子集之间的联结主义区分所取代。如果这一点是对的,那么联结主义网络丧失了组合句法和组合语义提供的益处。又如果构成性是人类思想的本质特征,那么联结主义似乎没有能力处理那些涉及到思想的高阶认知过程。构成性问题于是提出了这一怀疑论见解:联结主义是否是对认知的正确探讨。
三、思想的构成性:联结主义的解决
有两种方式回答经典主义的挑战。首先,正如fodor和pylyshyn已指出的,没有结构上的原因为什么联结主义不能采纳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联结主义者可以发展其网络来处理表达的构成性问题。然而,在这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产生了:即使联结义网络能够实现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但据说联结主义者“不能既有一个组合表达系统又有一个在认知层次上的联结主义结构”(j.fodorand z.pylyshyn,1988,p.308).fodor和pylyshyn认为,允许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的联结主义系统只是对经典模型的硬件实现,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联结主义结构。其次,而且更根本的是,联结主义者可以质问fodor和pylyshyn论证的基础,即询问实际的认知活动是否显示了他们所认同的那种构成性。这就是说,联结主义者可以否认在联结主义系统中实现强构成性的必要性。为此,他可以表明要么语言和思想在强的意义上实际上不是构成性的,要么无须假设本身可由强构成性来表征的内在结构便能说明思想和语言的构成性。
强构成性是语义的构成性和构成要素的语境性的结合。从人们对日常语言的理解中很容易看出,强构成性与理解的语境敏感性不相容。因此强构成原则本身就值得怀疑。事实上,大量来自概念学习和概念组合理论的经验证据表明这种怀疑是合理的。这里我们需要以一种纯描述的方式来使用“概念”这个术语,即把概念看作是对范畴的主观表达,因此我们感兴趣的是人们用来范畴化范例或进行典型性判断的知识结构。作了这样的规定后,我们可以来评价fodor和pylyshyn的这一经验主张:概念组合过程在于从构成要素的于语境的意义中计算复杂表达式的意义。
第一组经验发现涉及到概念结构的不稳定性。由于f.rosch等人的工作,这一点已得到广泛接受:范畴不是按照必要的和充分的特点来表达的,一个特定范畴的范例可以沿着典型性的一个方面连续变化(e.rosch.1973)。结果,对概念的新近说明是按照原型、家族相似性或存贮起来的范例来进行的(e.e.ith and d.medin,1981)。l.w.barsalou考察了概念结构不稳定性的大量实例,其中发现,对一个范畴的成员的典型性判断对于不同的受试群体、对于同一群体的不同受试者,甚至对于处于不同时期的同一受试者都是不同的。由此他推断说:“逐级渐变结构并不反映概念的不变性质。……而是,人们使用的概念是从长期记忆的知识中,由一个敏感于语境和新近经验的过程构造出来的”(l.w.barsalou,1987,p.135)。这些发现有力地表明,对一个特定范畴的表达是随着目前的和过去的语境变化的。概念是根据长期记忆的知识灵活地构造出来的短暂的记忆结构。什么信息被整合进入一个范畴的特定表达中,这取决于能否得到存贮在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语用的、语义的词汇的语境,以及视野、目标和意图都在调整着用来构造一个特定范畴表达的知识。
概念结构的不稳定性对概念组合施加了重要约束,确实,人们往往能够不费力地理解复杂概念或语句的意义,因此某些构成性似乎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强构成性是否确实表征了人们理解复杂概念的过程。早期的概念组合理论把复杂概念的外延处理为简单概念的交叉。现已表明外延理论作为心理学理论是不合适的。大量证据表明,一个复杂概念的实例的典型性通常不能从简单概念的典型性中预测出来的。概念的不同的特点方面是相互的传统假定已受到挑战,相反,在组合概念时,人们依赖于属性之间的相对复杂的共变模式,而这些属性是从人们对世界的一般知识中引导出来的(e.e.ith,et.al.,1988)。不难理解,概念组合的灵活性和语境依赖性也对语句理解施加了必要约束。有充分的理由假设语句意义的构造是几个知识源并行相互作用的产物(w.marslen-willison and l.k.tyler,1987)。
所以,如果我们发展一个心灵的计算理论,该理论公正地对待常识心理学的见识,那么这个计算框架必须既能处理信念内容的构成性(信念是由有内容的要素构成的),又能处理这些构成要素的语境敏感性(信息的构成要素具有部分地由包含它们的语境决定的内容)。经典符号主义在能够实现第一个要求时,似乎不太有能力实现第二个。相比较,具有分布式表达的联结主义网络似乎能在一种弱的意义上调和这两个事实。这里,关键的思想是约束满足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构成要素的意义是以敏感于语境的方式渐变的,以便使最终得到的复杂意义的整体连贯性达到最优。语境的敏感性来自于两个源泉:首先,包含一项特定的语言信息的外部语境输入会改变定义在网络状态上的能量函数,从而调整网络将收敛到的稳定状态;其次,隐藏单元不仅从输入单元接受激活,而且也从网络内得到激活。结果,对一个特定输入的响应将多少随着当前的内部语境输入而变化。另一方面,在联结主义系统中,复杂表达式能够由一些网络或单元集的协作活动产生,每个网络或单元集贡献了一个构成部分。由于每个这样的构成部分本身是网络的整体活动的产物,所以复杂的联结主义表达可分解成为真正具有内容的构成要素。这里应注意的是,在联结主义网络中,语义解释的基本对象是单元集,而不是个别单元。
联结主义的这一解决不丧失语境的敏感性,同时又阐明了这一点:简单表达式的语义内容确实对复杂表达式的语义解释做出了贡献。然而,约束满足网络并不允许这一意义上的真正的句法构成性,即构成性是受纯粹的形式规则支配的。所以严格地说,p.olensky所启示的这条解决路线并没有真正地解决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的问题(j.fodor and b.mclaughlin,1990)。另一方面,如果构成性原则是一个经验假说,那么经典主义者所设想的这种构成性似乎不适合作为一个心理过程理论。所以在我看来,经典主义和联结主义在思想的构成性问题上的争论仍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经验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尤其取决于常识心理学的见识,取决于对人的认知结构本质的探究。
参考文献
barsalou,l.w.(1987),"the instability of graded:structure:implicationsfor the nature of concepts,"in concepts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ed,u.neisser,cambrdge university press.
churchland,p.m (1981),"eliminative materiali and propositionalattitudes",reprinted in churchland (1989).
churchlaud,p.m. (1989) a neurocompurational perspective.the mit press.
feyerabend,p.(1963),"materiali amd the mind-body problem".review of metaphysics,94.field,h.(1978),"mental representation."in readings in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vol.2.ed.n.bloc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dor,j.a.(1975),the language of though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dor,j.a.(1987),psychosemantics.the mit press.
fodor,j.a.and mclaughlin (1990),"connectioni aud the problem of systematicity:why olensky's solution doesn't work,"cognition,vol.35(2).
fodor,j.a.and pylyshyn,z.(1988),"connectioni and cognitive architecture:a critical ysis,"cognition,vol.28 (1-2).
marr,d.(1982), vision,freeman and co.
marslen-willison,w.and tyler,l.k.(1987),"against modularity" in modularity in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language comprehension,ed.t.l.garfield,the mit press.
minsky,m.(1981a),"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in mind design,ed.j.h.haugeland,the mit press.
minsky,m.(1918b),"k-lines: a theory of memory," in perspectives on cognitive science,ed-d,norman,n.j.,ablex
ramsey,w.,stich,s.and gardon,j.(1990)."connectioni,eliminativi and the future of folk psychology," in folk psychology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eds.s.m.christensen and d.r.turner,n.j.,lea publishers.
rumelhart,d.e.,mc clelland,j,l., and the pdp research group (1986),parallel distributed proessing,the mit press.
rorty,r.(1970),"in defense of eliminative materiali",review of metaphysics,24.
schank,r (1981),"language and memory," in d,norman (ed).
ith,e.e.,and medin,d.(1981),categories and concep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th,e.e.,et.al., (1988),"combining concepts: a selective modification model,"cognitive science, 12.
olensky,p.(1987),"the constituent structure of connectionist mental states: a reply to fodor and pylyshyn,"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6 (supplement).
stich,s.(1983),from folk psychology to cognitive science,the mit press.
winograd,t.(1981),"what does it mean to understand language," in d.norman (ed ).
语言、意义、与蒯因的不可限定说_其他哲学论文 第十篇
摘要:蒯因提出翻译不可限定说,指出翻译语言没有限定的对译守则,用意在于说明受话者依照不同的翻译守则去理解说话者的语言,得出不同的理解有可能是等效的;也就是说,各个受话者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完满地解释并且预测说话者的言行。蒯因的这个主张引起疑虑,人们担心受话者所理解的可能不是说话者的想法。本文修订了蒯因的观点,让疑虑消除。(1)先维持蒯因的观点, 认为受话者认识说话者的想法在于所依据的理论能够完满地解释并且预测说话者的言行;(2 )指出这个观点虽然否定了于理论的句义,却没有否定于理论之外的语言,语言离开理论还有所表述;(3 )指出受话者即使没有得到有关言行的理论所指引,仍然可以依照语言习惯掌握说话者所要表述的想法。
关键词:语法 组成规则 转换规则 语义 内涵的概念 检证 验证 观察语句 翻译不可限定说 翻译守则 限定不足说 科学理论上的整体主义 意义上的整体主义 性的假设 翻译语言 条件反应说 意义上的唯我主义 意义上的怀疑主义 移情作用 极始翻译理论 单辞句 意指词 意指对象 意指机制 个体名词 堆块名词
(一)导论
语句(或者一组语句)表述的是甚么东西?卡纳普(carnap)的答案是“意义”;他主张认识语言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它的语法,语法包括了句子的组成规则和句子之间的转换规则,语言得到使用应时当根据这些规则识别所采用的合法语句以及从这些语句推演出来的其它语句,再按照语法和语义的规订识别合法语句所表述的意义,便掌握了这个语言。wwW.meiword.com〔1〕蒯因(quine)在卡纳普写好了《语义学导论》〔2 〕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他不会被卡纳普所说服,而且在这几十年间陆续提出了反驳的论证;〔3〕不过,反对的方式和理由却先后有变, 形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五十年代初期,《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扼要地铺陈了他的看法;他指出“意义”是个内涵的概念(intensional meani ng),除了让别的内涵概念来说明它的意义之外, 就没有别的方法可 用于说明它是什么,问题在于别的内涵概念也依靠着“意义”来说明,所以蒯因不相信“意义”是个明确的概念,足以用来说明语句所表述的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4 〕更何况语句所表述的要视乎它怎样配合其它的语句合力表述一个不抵触经验的科学理论,因此它从来就没有(于理论)的意义,为事先约定的语义规则所确定下来;〔5 〕经验主义者相信内涵概念的魅力和语句意义,就相信了两个教条。为什么是教条主义而不是金科玉律呢?蒯因可以拿出这样的解译:经验主义者讲求检证,而检证所针对的是理论中的语句,这些语句没有的意义;所以,经验主义者应当否决的语句意义,这个否决的态度还要贯彻到只有使用别的内涵概念才有可能但最终不会说得清楚的“意义”;因为说明这个概念的理论如果是正确的,它应当和其它的科学理论一样,包括了一些可直接验证的观察语句;采用这样的理论来说清楚的概念当然有别于上述的内涵概念,而经验主义者没有理由接纳后者。
不过,揭示卡纳普的两个教条,并不等于全面否定了卡纳普的意义论,有些语言哲学家依循着他的步伐,提出语义学,并把它视为形式科学,以“意义”为研究对象,这些哲学家当然推崇卡纳普的意义论,却不为《教条》一文所驳倒,因为他们不必是经验主义者;〔6 〕因此,蒯因有必要进一步交代清楚为什么直接掌握有关的内涵概念却仍然说明不了(一组)语句所表述的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要等到第二个时期才有答案。
第二阶段的主要见解集中于六十年代出版的名著《言词与对象》;〔 7 〕他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不可限定说( the thesis of translational indeterminacy),直接以翻译部落语言出现众多等效的版本为例,先指出没有超越于翻译的语义规则限定了部落语句的意义,再据此推断没有这样的意义作为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卡纳普的意义论遭到遗弃,主要不在于这个理论偏离了经验主义,而是在于设想了一些东西,却无助于说明语句所表述的是什么。
第二阶段的论说不容易掌握得好,以前蒯因要先说明科学理论的整体性,藉此说明理论所包括的语句没有的意义,才进一步说明卡纳普的意义论因为设想了没有其事的语句意义,偏离了崇尚科学的经验主义而当予扬弃;即使出版了上述的名著之后,许多人仍然把翻译守则(translational manual)和解释部落言行的科学理论等同起来,根据理论的整体性来说明为什么有关的言行没有充分限定(under-determine)翻译守则,然后根据限定不足说(the thesis of underdetermination)论证没有超越于理论的意义;也就是说,语言在表述理论时才表述意义;因此,说明语言所表述的是什么便等于说明语言表述理论时所表述的是什么;那么,学习语言离不开学习语言所表述的理论;如果是这样,他们除了承认原先已经接受了的科学(理论)上的整体主义(scientific holi),现在又承认意义上的整体主义(meaning holi) ,即承认语言学习者要掌握理论的各个部分才可以掌握理论的一部分,并且承认要通盘掌握语言和理论才可以掌握语言;如果这些人能够充分认识蒯因的翻译不可限定说在于否定超越于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指证语言离不开理论,以为离开了就成不了表述媒介;那么,就不会轻率地认为蒯因的学说在于鼓吹意义上的整体主义。当然,造成误解,蒯因本人也有责任,这是由于他表示过认识对方的语言,主要目的在于理解对方的思想,而确认对方的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在于确认对方所用的真语句;没有掌握这些真语句,即没有掌握这些真语句所表述的理论,便不算认识对方的语言;因此,有理由相信蒯因接受了意义上的整体主义;这意味着蒯因也没有法子分开处理语言和理论表述什么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这是为人疚病的地方;本文试图从他的主要论说中找出理据,略作修补,然后据此证明语言和理论要分开处理,才可充分领会翻译不可限定说的用意。
(二)反对意义上的唯我主义
开展这项工作可从他的设想谈起,他把语言学习者设想成翻译者,把学习过程设想成追寻正确翻译的过程;为了掌握正确的翻译,翻译者要做个称职的语言学家,从事实地考察,搜集部落人士的言行资料;并且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建立性的假设(anlytic hypotheses),让这些假设为部落言词或者简单的语句配上翻译的言词或者语句,而这些假设组合起来就成为翻译守则,守则正确与否就以是否符合上述的言行资料为准;蒯因的设想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衡量科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方法大体上都适用于衡量守则是否正确,这有助于我们明白为什么有完整的言行资料,也不足以限定翻译者当选取那一个守则;提出翻译者有众多等效的翻译版本可供选择,如果不是为了全面否决‘意义’而铺路,至少提醒我们,翻译者如果没有选定翻译守则,就确定不了部落语句所表述的是什么意义。只要翻译者首先根据选定的守则拟定部落言词或者语句的翻译(言词或者语句),再根据后者在科学理论中的地位来确定它们的意义,便可以藉著互译言词或语句的等义关系来确定部落语句的意义;如果确定的结果没有抵触部落人士的言行,有关的守则便算正确,所确定的部落言词与语句的意义也算正确。如果翻译者因此而认识了部落语言;那么,他所追求的就不是超越于翻译守则的意义,而只是内在于科学理论的意义;这个的优点在于消除了超越于守则的意义,缺点就在于承认了内在于理论的意义,并且让这个意义观来说明语言学习的情况。
按照蒯因的论述,外族人要通过翻译守则去掌握部落语言,而守则所确定的意义取决于翻译者预先确认的科学理论——尤其是用于解释或者预测部落言行的理论;鉴于部落言行没有充分限定理论和守则,翻译者完全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论为部落语句的翻译和意义而各言其是;有多少个理论经得起检证,部落语句就有多少个不同的翻译和意义;至于部落人士虽然不必通过翻译来认识母语,也要有自己的理论,据此以确定母语语句的意义;所以,部落人士所掌握的也是内在于理论的意义;由于所有的理论,不管是部落人士提出来的,还是翻译者提出来的,只要经得起检证,便具备了同等的权威;因此,部落人士没有占着更权威的位置,好让他宣称自己比翻译者更了解部落语言;那么,通过学习怎样翻译部落语言来掌握这个语言,所要认识的不是内在于那一个特定理论的意义,而是翻译者随机审度了部落言行之后而制定了用于解释或者预测言行的理论、以及内在于这个理论的意义。蒯因如果真的让守则和科学理论等同起来,只要凭着限定不足说来否定了超越于理论的意义,就可以拿着同样的不足说来否定超越于守则的意义;如果蒯因真的以理论没有受到充分的限定来说明意义没有受到充分的限定;那么,他除了说明部落语言没有超越于理论的意义为人所掌握之外,也说明了部落人士为自己的语句所拟定的意义并没有特殊的地位,为外族翻译者所掌握。根据这样的,认识部落语句的意义,就说不上是认识了部落人士所表述的特定意义——例如认识部落人士使用“gavagai ”这个句子时所要表达的意义;这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个论调鼓舞了意义上的唯我主义(meaning solipsi);翻译者和部落人士使用同一个部落 语言,任何一方只能够依据自己所掌握的内在意义来解释对方的语句,这样能够通过对方的说话来了解对方的思想吗?相信蒯因不愿意鼓吹唯我主义,在限定不足说以外,他还提出了不可限定说,这显示了他有别的看法。
蒯因提出不可限定说,指出部落语句本身谈不上有什么意义翻译者要予以确认;那么,把部落人士或者翻译者掌握部落语言的情况说成是各人掌握了各自拟定的内在意义,以为蒯因赞成意义上的唯我主义,这显然是个误会;让我们从他的论说中整理出一个不含误解的:制定单辞句“gavagai”,让它指称(refers to)兔子,翻译者须要拿出理由来;只要他应用条件反应说,指部落人士看到兔子掠过便说出“gav agai”,或者应用别的学说,把“gavagai”和兔子联系起来;便有充 分的理由让“gavagai”解作“兔子”;这表明了认识“gavagai”的指称,实际上是知道怎样依靠科学适当地解释部落人士的言行;除此之外,翻译者没有也不必掌握其它的知识;也就是说,翻译者制定的守则实际上没有和科学理论一起,为“gavagai”的指称提供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唯有让科学的解释单枪匹马为“gavagai ”寻求它的指称,这就注定了“gavagai”的指称无以限定; 至于卡纳普的追随者认为部落人士为了掌握母语而需要掌握的意义,以及语法和语义规则等,翻译者是否也需要掌握完全在于部落言行得到解释时是否需要设想这些东西;如果认为有必要设想这些东西,这只能是科学上的考虑,翻译者参考有关的科学便可以断定所设想的是什么东西,不必再参考翻译守则;如果没有必要设想这些东西,则当予扬弃,这同样是科学上的考虑,与守则无关;总而言之,认识语言实际上是决定依据着那一种有效的言行解释来翻译部落语言;言行的解释尽管没有充分限定守则,也有所限定;不要以为翻译守则本身不受言行解释的左右,为我们所直接掌握,并据此以确定部落人士的思想和行为起着什么作用,这就是不可限定说的主要论点;也许我们有一个好的言行解释,方便我们确定“ gavagai”的指称;不过,由于相同的言行解释可以蕴酿出相异的守则 ,解释本身限定不了指称,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内在于这个解释的意义了;因此,掌握了关于部落言行的解释,并据此制定翻译守则,从而认识部落语言,并不是因为掌握了(可为解释所限定的)部落语句意义;不拿内在的意义来说明一个人掌握了部落语言,便避免了唯我主义的谬误;指出翻译者并非唯我主义者的论证实际上支持了意义上的怀疑主义(meaning sceptici),因为支持这个论证实际上主张部落语言如果表述了意义,所表述的一定是可限定的意义;既然意义不可限定,那么,语言所表述的根本不是(可限定的)意义。幸好翻译者掌握部落语言不在于掌握部落语句的意义;所以,他一方面不必忧虑所掌握的仅是自己所拟定的内在意义,而触犯唯我主义的谬误;另一方面又不必忧虑意义不可限定而掌握不了部落语言,接受意义上的怀疑主义不等于接受了语言学习上的怀疑主义。事实上,蒯因不止一次清楚地表明了语言存在于社会,〔8〕并不存于个人的内在世界里, 因此接受不了语言的唯我主义,也接受不了语言上的怀疑主义;如果是这样,蒯因有必要说明学习语言所要掌握的是什么东西,回答这个问题,要先知道部落人士使用部落语言所表述的是什么。
(三)语言、意义与解释言行的理论
蒯因没有直接回答上述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仅仅追问部落语句所表述的是什么,以为这样提问便等于追问部落人士使用部落语句时表述了什么。本文的主要目标在修补蒯因的主要论说,并据此处理部落人士所要表述的是什么,让我们得以根据他们所用的部落语句推断他们的想法。需要修补的论说包括了以下两点:
1.蒯因相信部落小孩和长辈们有着相同的生理和心理结构,理应与长辈一样,能够根据来自发音和掠过的东西的在移情作用底下,认识长辈们以“gavagai”指称着兔子(或者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 the undetached parts of a rabbit)。这个想法一方面让人们明白部落人士为什么不经思索,便同意了以“gavagai ”指称着兔子(或者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在指称方面取得共识;另一方面,又可以解释为什么别疑“gavagai ”是否指称着兔子(或者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时,无论小孩和长辈们只要懂得条件反应说,都可以引用它来解释大家为什么同意以“gavagai ”指称着兔子(或者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在指称方面取得共识。我们还要进一步补充这个观点,指出小孩和长辈们即使放弃了条件反应说,在新的解释还没有形成之前,也可以依循既有的习惯继续以“gavagai ”指称着兔子(或者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维持指称上的共识;换句话说,小孩和长辈们不必预先在怎样解释部落言行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才可以为“gavagai ”取得指称上的共识;既有的习惯取代了解释上的共识,为指称共识提出保证;尽管解释怎样认识部落语言离不开解释部落言行的理论或假说,这不等于表示了语言离开了(解释言行的)理论,就无所表述。
2.蒯因提出不可限定说,否定了于翻译守则以外的意义,为某个翻译守则所‘捕捉’;因此,翻译者认识部落语言,不在于追寻某个特定的守则,藉此‘捕捉’部落人士所表述的意义,而在于恰当地解释或者预测部落人士的言行。我们还要进一步补充这个观点,指出翻译者追寻翻译守则,藉此认识语言;不仅在于寻求适当的理论,完满地解释部落言行;在既有的理论受到摈弃,新的理论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翻译者还要懂得在什么情况下继续尊重既有的语言习惯,以“gavagai ”指称着兔子(或者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才算得上认识部落语言。为了说明尊重既有的语言习惯并不是坚持解释部落言行的一些理论或假说,只是坚持了语言不必依附于这些理论或假说才有所表述;我们要清楚地指出翻译不可限定说所否定的仅限于于理论以外的意义,并没有否定于理论之外的语言;尽管语言不表述内在于理论的意义,离开理论它还是有所表述的。
上述的修补没有抵触蒯因的限定不足说和不可限定说,他应当承认语言不必依附于理论才可表述说话者的意思,说话者当可限定语言的用法。在下一节里,我们先引用蒯因的例子,重述他的主张,指出受话者要先有假说,解释说话者为什么说出“gavagai”,才认识“gavagai”的指称;然后探讨这个主张的含义,指出认识指称的先决条件使受话者避免不了限定不足和限定不了的情况,最终导致指称分歧,为语言交流制造障碍;跟着的一节则优先讨论这个想法究竟有没有根据,这样做有利于清除指称分歧所造成的疑虑和澄清不可限定说的含义,让我们明白说话者为什么能够限定意指。
(四)限定不足和限定不了的情况与指称分歧
为方便解答语句表述什么这个问题,蒯因刻意讨论比较简单的单辞句(one-word sentence),例如他经常提到的“gavagai”,就被想像为某个部族的单辞句,它所表述的要视乎我们按照那一套(已证明为)可行的翻译守则去翻译部族的语言才可以确定下来;也许存在着守则甲,让“gavagai”译作“(这是)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 以前者指称后者所指称着的东西;而另外还有守则乙,让“gavagai ”译作“(这是)兔子”而指称着后者所指称着的东西;在蒯因看来,谁能够凭着部族的说话而明白该怎么样跟部族人士打交道,以便得到预期的效果,谁的守则便算是正确的、或者是可取的;接受这个取舍的标准,就得同意甲乙两守则有可能同为正确,这样得来的守则又怎样帮助翻译者认识部落言语呢?
如果选择从“gavagai”这个单辞句入手,去认识部族的语言; 最适当的做法是依据目前最可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特别是心理学方面的做法,去确定说出了“gavagai”的部族人士产生了那些条件反应, 再根据这些条件反应去确定“gavagai”所表述的是什么。 按照目前认可的心理学, 如果我们证实了在眼前一掠的东西驱使部族人士说出“ gavagai”,我们会同意这是个发生了条件反应的情况。 认识这个反应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gavagai”所指称的正是掠过眼前的东西, 这不等于说认识这个条件反应就可以确定掠过眼前的东西正好是“gavagai ”所指称的兔子;不要以为知道了这东西是兔子,又知道了这东西驱使部落人士说出了“gavagai”, 便以为可以顺理成章地知道了有关单辞句所表述的是什么;我们还要进一步确定如果不这样想,我们所掌握的心理学知识既解释不了说话者的言行,也促进不了语言交流;才可以同意:说出这个单辞句的说话者因为相信掠过眼前的是一只兔子,而且相信“gavagai”指称这个东西,才说出这个单辞句;并且接受“gavagai”译作“免子”为翻译守则。做好这一步工夫,擅用守则,才算得上真正确定了这个单辞句所表述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并且认识“gavagai ”的指称,自己要有一些看法,例如赞成条件反应说,认定掠过的东西为兔子;解释部落人士为什么说出“gavagai”以上述的看法为据,便 不得不让“gavagai”翻译为“兔子”;如果别人有另外的想法, 例如认定掠过的东西为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他也许要把“gavagai” 翻译成“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才可以恰当地解释部落言行;〔9〕 只要两人有着等效的解释,两个翻译就有着相同的地位,这个情况蒯因称为限定不足的情况(a case of under- determination);别人根据“gavagai ”译作“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这条守则来解释或者预测说话者的言行,完全有可能跟我们一样恰当地理解说话者;这反映了说话者的言行没有充分限定那一条守则可用于解释这些言行;情况虽然如此,却不妨碍我们通过翻译守则去认识说话者的语言。因为科学家和受话者都以相同的证据为基础。〔10〕前者不会因为所有的证据没有充分限定掠过眼前的东西是一只兔子的假说便以为他的假说无助于认识大自然;同理,后者不应该因为所有的证据没有充份限定“gavagai ”指称着什么而以为自己的翻译守则无助于认识说话者的语言。
如果受话者真的犹疑不定,决定不了“gavagai ”指称“兔子”还是“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所指的东西,这绝不是因为证据与翻译守则之间存在着改变不了的限定不足的情况,而是因为受话者还没有选定翻译守则;除了科学家也考虑的证据之外,再没有别的证据可以左右受话者的选择。〔11〕在一般的情况底下,所得的证据如果促使科学家确认说话者说出“gavagai”是兔子掠过眼前所造成的条件反应, 也当促使受话者确认“gavagai”指称“兔子”所指的东西;另外, 所得的证据如果促使科学家把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和“gavagai”联系起来, 视为条件反应的情况,也当促使受话者确认“gavagai ”指称“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所指的东西;不过,在证据面前,科学家和受话者不必依循刚才所说的一样,来个协调的选择;也许受话者同意一些科学家们的假说,认为掠过的东西是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并且同意说出“gavagai”是这个东西所促成的条件反应;虽然如此, 受话者仍然可以坚持“gavagai”指称兔子。 这些科学家所承认的事实限定不了受话者的选择,也限定不了说话者的选择,这个情况蒯因称为限定不了的情况(a case of indeterminacy)。如果说话者和科学家的选择不协调, 而且不为受话者所知,就很难想像受话者无误地掌握了说话者的语言。
让我们从蒯因的观点出发,说明这是一个什么的疑难;按照他提出的极始翻译理论(theory of radical translation), 受话者如果要知道“gavagai”指称着什么,便先可有一个假说, 解释说话者为什么说出了“gavagai”这个单辞句,即确定究竟说出了“gavagai”是兔子、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所造成的条件反应;有了结论便可以凭着它确定“gavagai”指称兔子、 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还是其它的什么东西。情况如果是这样,纵使受话者因着一些莫明的力量,知道了说话者以“gavagai”指称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受 话者也不能够据此确定说话者在反省自己的心理变迁之后便会相信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造成了自己说出“gavagai”的条件反应; 除非受话者也有相同的假说,并借此确定“gavagai ”指称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这表示了受话者总不能够没有假说便有了翻译守则。他的假说也许为说话者所认可;那么,两人以“gavagai ”指称同一事物的成数就很高;也就是说,如果两人都认为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造成了上述的条件反应;那么,两人在承认相同的假说之余大概也会承认所指称的是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不过,受话者为了认识说话者的语言而预先制定的假说却很可能有异于说话者或者他的社群原来所认可的假说而终至各言其是,例如受话者认为兔子在眼前掠过促使说话者说出了“gavagai ”,而说话者却认为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造成了上述的条件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两人说出“gavagai”时就很可能指称着不同的东西, 受话者可能指称着兔子,而说话者则可能指称着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如果不同的假说真的导致了指称方面的分歧;那么,让受话者按照说话者的想法修改自己的假说,是否可以消除分歧呢?按照蒯因的,受话者不可能没有假说便预先知道说话者以“gavagai ”指称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受话者一旦有了假说之后,便只能够按照假说推断“gavagai”的指称;除非受话者的假说没有恰当地解释说话者的言行,否则 便不需要修改。受话者就算因为没有完满地解释说话者的言行而修改原有的假说,得出的新假说也不一定要求“gavagai ”指称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总之,部落人士和翻译者都需要先有自己的看法,才认识“gavagai”的指称;如果两人有着不同的看法, 实在没有什么方法保证指称的共识,“gavagai”注定没有可限定的指称。
蒯因如果要克服指称分歧,让受话者知道说话者的指称,他应当清楚地说明受话者怎样使自己明白说话者的(科学)假说,并以此为基础,解释他为什么说出“gavagai”。 让我们在第五和第六两节中讨论蒯因应该怎样回应这个要求;第五节将集中讨论学习母语时小孩怎样争取指称上的共识,使他明白了长辈们以那些假说来解释自己的言行;并且进一步讨论小孩们在长辈们放弃了原来的假说之后,怎样维护既有的语言习惯,保持指称上的共识;第六节则集中讨论翻译不可限定说,指出它所否定的是脱离任何假说的意义,没有否定脱离假说的语言;澄清这一点,才可以说明小孩和长辈们在没有假说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够保持了指称上的共识,让说话的一方继续按照共识限定“gavagai”的指称 。
(五)相干的假说和意指共识
说话者(过去)通过长辈而外族的受话者则通过翻译学会了怎样正确地使用说话者的指称词(referential terms )说出了他们所认识的指称对象(referents), 两人都以指称词使用者(长辈或部族的成年人)的言行为材料,从中归纳出一套指称机制(the machani of reference),确定这个机制囊括了那些指称词和那些指称方式,以及 确定了那些指称词在那些上文下理中采用了那些指称方式而起着指称的作用。例如学习怎样使用单辞句“gavagai”,让它起着指称作用, 学习者要根据所知的材料确定它在那些上文下理中究竟是以(指称分立的)个体的名词(individual terms)、抑或以(指称可聚散的)堆块的名词(mass terms)的身份或指称方式而起着指称的作用;〔12〕知道了指称词的身份或指称方式,学习者可以据此进一步确定指称词的指称对象,看看得出的结果是否妨碍原有的假说,使它无法完满地解释长辈或者部落成年人的言行。
这个整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学习怎样使用指称词的过程。确认周围的环境中那些东西驱使说话者说出了例如单辞句“gavagai ”的说话最多可以说明说话者的反应证明他有能力辨别类似的东西是否重视,还没有说明单辞句是怎样起着指称的作用(即以什么身份或指称方式指称对象);要说明这一点,外族的受话者有必要建立一个完备的翻译守则,通过守则确定部落语言的指称机制,并据此确定指称词在什么的上文下理中采用了那些指称方式,从而确定单词句“gavagai ”是怎样起着指称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受话者和说话者的两个机制很可能有分别,在说明彼此的本体论(ontology)时让不同的机制发挥作用,便会出现了两个本体论,关乎指称对象的结构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是这样,受话者纵使使用了说话者的语言,却指称着不同的对象。〔13〕
指称分歧真的难以避免吗?按照蒯因的,部落小孩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小孩们开始学习部落语言,学的就是母语,这个时候还没有掌握别的语言,所以不靠翻译来理解长辈的语句;他们只能够靠着对谈并在对谈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直至大家觉得对谈增进相互了解的时候,才算理解长辈的语句。〔14〕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小孩们逐渐学懂了长辈的指称机制;如果谈到大家的想法当中有什么东西被想像为存在的时候,就让这个机制发挥作用;那么,小孩和长辈当有相同的本体论,致使两人在同一的上文下理中用上相同的指称词时只要意识到所用的指称方式相同,便可以确认有关的指称词指称着同一的东西。小孩们除了没有事先掌握任何指称机制(和本体论)而避免了指称分歧之外,他们也没有事先掌握任何(科学)假说才开始学习母语(即部落语言),因此又避免了假说分歧,这有助于掌握部落语言的指称机制,过程是这样的:他们在对谈中逐渐掌握指称机制时也逐渐掌握了长辈们的一些假说,用来解释为什么长辈们说出了例如“gavagai”等的单辞句, 让这些恰当的解释巩固他们在指称机制方面的知识,同时又反过来让后者巩固前者,直至小孩们成为成熟的说话者。
成熟的特征就在于明白指称机制和(科学)假说之间在什么时候互相配合、什么时候两不相干。如果前辈们一方面认为“gavagai ”指称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另一方面却相信促成他们说出“gavagai ”的是掠过眼前的兔子;成熟的说话者会根据长辈们的指称机制确定“兔子”指称着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另外会根据长辈们的假说解释长辈们之所以说出上述的单词句是由于兔子在他们的眼前掠过;成熟的说话者不会以上述(长辈的)假说说明(长辈的)指称,也不会认定(长辈的)指称机制配合上述(长辈)的假说,因为他知道长辈们没有根据指称来拟定假说,“gavagai”根据别的假说来确定它的指称。 知道什么情形下指称和假说两者互相配合、什么情形下互不相干,便有能力以说话者的假说来解释说话者的言行,也有能力借助说话者的指称来确定他们的想法,包括他们所认许的假说(这包括了以前就想过和以前没有想过但一经别人提起便同意了的假说)。按照蒯因的想法,能够达到这个境地,很大程度上靠着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移情作用,设想自己在长辈们的处境中以长辈们的态度来对待指称和假说。〔15〕
究竟在移情作用下孩子们走上了怎样的学习历程、使他们恰如其分地掌握了指称和假说的关系呢?蒯因认为学习母语的部落小孩像个(初出茅芦的)科学家,以长辈的言行为材料,从中整理出一些假说,用来解释长辈们的言行;如果长辈们都在兔子出现时才说出“gavagai”, 部落小孩不必知道长辈们相信“gavagai”指称着那些东西, 小孩们甚至没有指称词说明掠过眼前的是什么东西,仍然可以就这个模糊的东西提出假说,解释长辈们的言行;这个时候的解释当然是模糊的,但是,孩子们不竟是靠着这个模糊的解释勉强地算是明白了长辈们为什么说出“gavagai”来; 纵使小孩们不知道这个模糊的东西实际上是长辈们所指的兔子,也不妨碍长辈们认同这个模糊的假说;只要日后孩子们确认了这个模糊的东西的确是兔子,我们便有理由相信小孩们提出的假说原则上可以成为长辈的假说;也许长辈们所指称的原来是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在这种情况下,小孩们一直沿用的假说尽管能够恰当地解释了长辈们为什么说出了“gavagai”;可是, 他们的假说却无助于确定长辈们所说的“gavagai”指称着什么; 因为孩子们的假说所预设的并不是长辈们原来所拟定的指称对象,所以无法引导孩子们认识“gavagai ”当指称着什么,成不了相干的假说;如果学习指称词的用法离不开相干的假说,小孩们便要尝试找出“gavagai ”在长辈们的说话中以那些指称方式发挥指称作用,并且据此追寻相干的假说,解开指称之谜。
让我们设想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情况:由于出现了特殊的情况,某个汉语部族处于一个从来与外界隔绝的自然环境里;那里,近百年来一直没有再找到自然出生的兔子,幸好部族的动物园里还保存了一只人工繁殖的雄兔,族人非常珍视它;而部族的科学家们早就想出了先进的办法来抢救这种几乎灭绝的动物,设立了近七十年的兔工场一直以先进的科技模拟兔子各个部分培养出与之符合的生物组织,并且把它们连结起来成为活兔;其实在大批量生产之前,部族科学家们曾经取下人工繁殖出来的兔子的一些部分,和培养出来的一些生物组织合成活兔;因此,这些人造的生物组织一直被视为兔子的各个部分,由这些组织连结成的活兔除了因为技术上的缺憾而没有得到生殖能力之外,其它各方面和自然出生的兔子没有分别;因此,这些以汉语为媒介的族人们继续使用单辞句“兔子”指称这种外表(以至内部都)无别于动物园里的那只兔子;虽然如此,族人还是改变了一些习惯,指称兔工场的兔子(的各个部分的连结体)时除了依循旧习惯,像指称人工或自然繁殖的兔子时一样,容许在指称词前面冠以“只”这个量词;另外,指称兔工场的兔子(的各个部分的连结体)时还可以在指称词前冠以“个”这个量词;也许部族有严格的生物工程法律,规定兔工场只准生产族人目前称为“兔子”的东西,即只准生产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因此,部族科学家需要弄清楚工场里与兔子各个部分相符的生物组织结合起来而成活的动物是否为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于是定期检查工场,认为合格便竖起拇指连声说道:“兔子”,“一个个的兔子”。
部族的小孩们如果让这个称心的检查结果来解释前辈科学家们为什么说出“兔子”,便正好预设了“兔子”的指称对象(即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从而得出相干的假说,这当然有助于确定检查员所拟定的指称对象。至于其它的假说是否相干,便要视乎情况而定;小孩们也许到过动物园,看到人工繁殖的兔子,并且听到了周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说出“兔子”,印象深刻,因此毫不犹疑地认为这只兔子引发族人说出“兔子”,并且依循着这个假说确认“兔子”的指称对象为兔子;所指称的虽然仅以动物园的兔子为样本,却包括了其它人工或自然繁殖而得来的兔子,也包括了从兔工场生产出来的兔子;这个想法能够说得过去,完全在于长辈们还没有区别对待繁殖得来的兔子和兔工场里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也没有想到调动量词的用法把两种不同的个体结构予以明确化;因此,人工或自然繁殖的兔子和兔工场里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仍然被视为同属一类,都称为“兔子”;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上述检查员和孩子们的两种假说同为相干(即以动物园和兔工场的活兔同为族人说出“兔子”的起因),当无问题。那个时候,小孩们提出假说,解释长辈们为什么说出“兔子”,无论是预设了人工或自然繁殖而得的兔子,还是预设了兔工场里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都预设了“兔子”的指称对象;只要按照这个相干的假说去确认“兔子”指称着所预设的东西,便知道了长辈们心目中所指称的是什么;这个时候,长辈和小孩们都没有想到采用“兔子”前面的量词来标明活兔的个体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让“兔子”一词覆盖原先没有按照个体结构的差异而予以识别的两种活兔,当然不算含糊。
不过,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变化,族人们除了保持传统之外,还采用了新的指称方式,指称兔工场的兔子(的各个部分的连结体)时让“个”这个量词放在指称词前面,却不让它用于指称自然或人工繁殖的兔子。借用“个”这个量词的新的用法来区分两种活兔除了要区分活兔的不同来源之外,也许要区分个体的一些不同的结构;像国家之类的组合体纵使成员全面更新也可以继续保持原有的身份,为族人所指称时都可以在它的指称词前冠以量词“个”;兔工场生产出来的兔子(的各个部分的连结体)是生物组织的连结体,如果也可以为它不断更新各个生物组织而使它活下去,族人便可以在它的指称词的前面冠以量词“个”;至于自然或者人工繁殖出来的兔子也许可以用兔工场的生物组织来替换逐渐衰败的各个部分而继续生存下去,却延续不了它原有的身分,因为它再不是珍贵的动物了;按照新生的习惯,就不应该把一只人工或自然繁殖的兔子说成是个兔子了。谁人知道了那些东西具备了像国家所具备的个体结构,(即知道了那些东西在撤换内部的组成部分之后仍然有可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身份,)便大有机会掌握“个”这个量词的新的用法;在掌握了新用法之后知道了它可以放在“兔子”的前面,便可以根据这个量词的用法确定了所指称的在长辈们的心目中当具备了上述的个体结构;这样便间接承认了动物园里的兔子由于没有具备上述的个体结构,原则上不应该在“兔子”以新的指称方式起着指称作用时成为指称对象;如果要保持着旧传统,继续容许使用“兔子”指称人工或自然繁殖的兔子,便要在指称词前面刻意标明“只”这个量词。不过,用量词做标记,不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从兔工场生产出来的东西在族人的心目中也像个个体;如果要标明它是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便要刻意地在指称词前面加上“个”这个量词;长辈们一旦确认了这一点,小孩们便要知道,如果根据动物园所见而得出的假说去确定“兔子”的指称对象,最多只能够确定长辈们为“兔子”一词附上“只”这个量词时所指称的是什么;如果小孩们不清楚这一点,就不能够确定长辈们所指称的是什么;不知道所指的究竟是一只一只从人工或者自然繁殖出来的兔子,还是兔工场生产出来的兔子的各个部分的连结体,这就出现了指称含糊的情况。
其实,小孩们开始学习母语的时候,(照蒯因的),碰到“兔子”的指称对象时,心中大概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这时听到长辈们说出“兔子”,便以此称呼这个模糊的东西;后来可能掌握了一些量词的用法,据此摸索出两种指称词,其中的一种指称着分立的个体,另外的一种则指称着可聚散的堆块;并且再按照量词的用法进一步确定“兔子”以前一种指称词的身份指称着本来是模糊而后来却具体化了成为个体的东西。〔16〕这是一个学习历程,连续根据刚掌握的语词用法把各种指称对象的本体论结构予以明确化;在不同的学习阶段里,指称对象在学习者面前呈现着不同的结构,在最初的阶段,“兔子”所指称的不过是一些模糊的东西,认为这些东西引发了条件反应,使长辈们说出了“兔子”,显然不会得到长辈们首肯;因为“兔子”指称的东西,在长辈们看来,再不是一些模糊的东西,就让这些东西给设想为个体化了的东西;也就是说,长辈们所愿意采用的指称词被视为指称着分立的个体;这意味着他们都倾向于相信个体化的兔子造成了上述的条件反应;这说明了孩子们不能够停留在最初的阶段,而是要向第二阶段进发,认识个体化和堆块化是怎样的一回事;掌握两者的差异才可以正确地认识长辈们的语言和想法;即正确地认识“兔子”(长辈们的单词句)是指称着分立个体的名词,又正确地认识长辈们以个体化的兔子来说明条件反应。蒯因认为小孩们进展到这个阶段当没有大问题;在他看来,这大概与他们的生理和认知的心理构造有关;〔17〕在这方面展开科学研究,蒯因相信可以进一步把情况交代清楚;让我们暂时把这个指称对象二分的观点看成是常识的观点;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把它看成是长辈们的常识观点;小孩们如果没有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或障碍,当具备了长辈们的常识观点;这个看法大致上符合了蒯因的观点。
小孩们在第二阶段中掌握了常识观点之后,便向第三阶段进发,设法认识长辈们怎样去调动量词的用法,让它们去标记在新的科技环境里值得注意的个体结构;其实,这个结构既不是新生也不是新发现的事物,像国家之类的组织向来都具备着这样的结构,即个体的组成部分全面更新不一定改变个体原有的身份;它之所以值得注意,原因在于新科技催生出来的活兔也具备了这个结构,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以往长辈们习惯了在“国家”前面冠以“个”这个量词,如果有人冠以“只”这个量词,他们就觉得不对;另外,谈到兔子时,就不反对冠以“只”字,这并不一定表示了长辈们刻意借助量词来反映国家和兔子具备了不同的个体结构,量词用法也许只是偶然形成的习惯,可能没有标记的作用;后来他们以对待“国家”前面的量词的态度来对待“兔子”前面的量词,就不应该再简单地视为偶然的习惯;也许长辈们从来没有想过个体结构,调动量词的用法可能有别的原因;不过,调动用法如果发生在新科技兴起的时候,调动以后又更方便于说明人们在新的科技环境中的问题和意愿,便有理由相信量词的新用法与新科技催生出来的活兔有关;再对比国家和新生活兔在那个方面是相同的,便很有可能使量词成为个体结构的标记,这样确认量词的新用法合情合理;也许外族的语言学家提出了另外的看法,据此而完满地解释了长辈们的言行,并因此(不得不)另立翻译守则,不以量词标记个体结构,这的确间接地说明了以量词标记个体结构的不比其它的为优越;蒯因提出翻译不可限定的主张,认为各个一旦完满地解释了长辈们的言行,就不会有事实方面或者意义方面的根据,裁定其中一个较其余的为优越;这个主张可以这样理解:即使长辈们谈到新生的活兔时有意让我们知道活兔的个体结构,也不一定要借助量词;因为没有所谓意义上的根据,让长辈们别无选择,以量词标记个体的结构;如果长辈们一旦选择了这种标记方式,也没有什么合理的根据阻止得了;长辈们的问题在于怎样使自己的语言发挥效用,让别人知道这个选择,是否得尝所愿要看小孩们是怎么样的语言学习者。小孩们学习长辈的语言,按照蒯因的,一开始就借助一些条件反应说确定长辈的单词句—例如“兔子”指称着一些模糊的东西;不过,这个假说很快便被修正了,本来预设了模糊的东西后来改为预设分立的个体;认为孩子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完满地解释长辈们的言行实际上是把孩子们想像成中规中矩的科学家,把学习语言和解释大自然视为同类的科学课题;〔18〕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这个看法最多说明了修正假说在于追求完美的解释,绝不能够说明修正假说在于追求相干的假说(即追求长辈们的想法)来解释长辈们为什么说出像“兔子”之类的单词句,从而更准确地识别单词句的指称对象;相信蒯因意识到上述观点的缺失,并为此作出补救,设想小孩们没有预定的想法和语言技巧,仅在移情作用下学习长辈们的语言;他们的首要目标显然不在于研究那些单词句指称着分立的个体,那些指称着可聚散的堆块;而在于设法与长辈们来个畅谈,双方得以畅谈大抵意味着小孩们逐步掌握对方的语言和想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时反省长辈们的单词句,好让自己凭着刚掌握到的语言技巧和关于事物的想法断定它们实际上是指称着个体、还是堆块;研究单词句凭着什么而有所指称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族人的常识观点,让(物理性的)指称对象分成个体和堆块两类;另一方面是语言技巧,说话时利用上文下理或语词的用法来指定单辞句以什么身份或方式起着指称的作用;蒯因大概相信一个具有常识观点而又愿意在移情作用下学习部族语言的小孩很快就能够采用长辈们的想法来解释长辈的言行。
这个有一个问题要交代清楚;蒯因所想像的语言学习过程在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两组,一组来自长辈们说出“兔子”时发出的声音,另一组来自模糊的东西;小孩们从长辈们那里学习母语,开始时要先学习长辈们怎样处理两组的关系,即学懂了凭着发音的找出了它所标记着的单词句,并且根据本身或者出现时周围的情况找出单辞句的指称方式,从而确定它所指称的究竟是个体、还是堆块;当发音的被视为确认有关单词句的可靠依据时,小孩们便要懂得来自模糊东西的已经成为确认有关指称对象的可靠依据了;两组的关系被理解为反映着指称词和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一个理据就是上面提过的常识观点,认为(物理性的)指称对象分成个体和堆块两大类,来自模糊东西的只能成为确认个体或堆块的依据;除此以外,别无确认;这正好对应着单词句仅有的两种指称方式(即意指个体和堆块的方式);没有个体堆块二分的常识观点,便无以整理两组的关系,让这个关系解释指称作用;蒯因似乎相信这个常识观点影响了长辈们的语言习惯,让单词句发挥指称作用时只能够在个体和堆块两大类中挑选一样作为指称对象。由于小孩们和长辈们有着相同的生理和心理构造,理应和长辈一样,能够根据来自发音和模糊东西的而识别有关的单词句和指称对象;长辈们和小孩们因着相同的而在语言的基础领域里形成了共识,受到蒯因的重视;他认为没有共识,小孩们和长辈们就不可能交谈起来。不过,蒯因也注意到在语言的基础领域内达成的共识阻止不了在语言的其它领域里出现分化;那么,要交代的问题就是:展开交谈之后,是否需要保持原有的共识,小孩们和长辈们才能够继续在交谈中明白彼此不同的见解?
设想小孩们从长辈们那里学习母语,刚完成了第二阶段,在单词句“兔子”的指称方式和指称对象两个方面和长辈们取得共识之后,准备进入第三阶段;奈何受到蒙蔽,不知道新科技催生的活兔已经面世,因此不知道调动量词的用意;也就是说,既不知道原来确认为指称个体的单词句进一步分化成两类,分别指称着的两种个体,彼此具备了不同的结构;另外,孩子们也不知道“兔子”不再泛指繁殖得来或者新科技催生出来的个体,而是配合单词句的分化结果而出现指称上的分化;那么,既有的共识给破坏了,新的共识还没有形成;小孩们凭着什么跟长辈们再畅谈活兔的情况呢?凭着什么知道了彼此之间出现了指称分歧呢?记得小孩们还在第一阶段,没有跟长辈们在“兔子”的指称方式和指称对象两个方面取得共识,争取交谈以促进了解就要靠所谓的常识观点,让小孩们依据这个观点确认掠过的东西为个体,并且确认它为“兔子”的指称对象;凭常识观点实现共识,蒯因是有信心的;因为成就共识的根据在于小孩们和长辈们有相同的生理和心理构造,这一点得到现有科学的确证;不过,学习母语进展到第三阶段,纯粹以生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并不足以解释小孩们怎样学懂了依循着新科技的发展方向,也不足以解释小孩们怎样学懂了把目光放在值得注意的个体结构上,从而确认个体名词的进一步分化,让“兔子”配合量词的调动分别指称两种活兔;因为文化的因素也影响着科技发展的方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为科技发展的方向不同而有不同的目光;至于文化背景相同的人也会因为不同的科学造诣而把目光放在不同的地方,影响了指称共识的建立。
为了重建共识,也许长辈们与小孩们对话时,前者需要担负更积极的责任;长辈们首先要注意那些假说,在学习母语的第二阶段里被用作依据,以确认两组的关系反应着“兔子”和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如果所用的假说应用了条件反应的学说,并且预设了繁殖得来的兔子或者在个体结构上与其相同的活兔,长辈们要做的第二件事便是清楚地告诉小孩们这个假说只限于解释为什么部落人士说出“兔子”,但不再用于说明这个单词句的指称对象;也就是说,长辈们有责任在对话中表明,即使他们同意单词句“兔子”的指称对象是根据常识观点而被确认为个体,并且同意一直以来都依据上述的假说去确认这个个体为一只(繁殖得来的)兔子;不过,长辈们还要讲清楚这个单词句已经进一步依据新科技的发展方向,并且得到量词新用法的配合,实现指称分化,以致原来的假说解释不了科学家检查兔工场后因为得到满意的结果而连声说道:“兔子、一个个的兔子”;纵使小孩们开始时不懂得兔子的繁殖问题,更不懂得新科技;因此,不明白科学家造访兔工场的目的在于检查另外一种的活兔,轻率地认定科学家谈论着繁殖而得的活兔;不过,这个误会是可以消除的;因为小孩们学习母语,已经进展到第二个阶段,相信有能力根据量词的新用法想到个体名词出现指称分化,再参照族人以不同的态度区别对待动物园和兔工场的活兔,便会逐渐明白单词句出现指称分化,与这种态度有关;长辈们和小孩们当可以凭着这个共同的见解重建共识,保持对话,使小孩们得以掌握长辈们大力开创的新科技和它的发展方向;并以新科技的观点去理解指称分化,说明指称分化不单只和族人的生活态度有关,还涉及新科技兴起后受到族人重视的个体结构。
如果长辈们真的能够在目前的对话中向小孩们说清楚新科技的作用,也许在将来现有的生理学和心理学被修正或者甚至被之后长辈们仍然能够向当时的小孩们说清楚掌握语言技巧其实不受共有的生理和心理因素所影响;到那个时候,常识观点本身也很可能因为孕育它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受到质疑而被搁置起来,即不再根据这个观点去确定掠过眼前的东西实际上是长辈们以“兔子”指称着的个体;这并不表示长辈们和小孩们在新的观点还没有形成之前无从决定“兔子”是否指称着个体,他们从来就知道许多与兔子有关的事情,就算放弃了常识的观点,“兔子”的指称对象也不至于变成为模糊的东西;尽管新的观点还没有形成,无以解释长辈们和小孩们如何在“兔子”的指称方式上取得共识;只要在生理学、心理学和常识观点等三方面所起的变化可以在长辈们和小孩们的对谈中交代清楚,小孩们完全有能力根据长辈们的想法来揣度“兔子”指称着什么;这样的交谈体现了双方在“兔子”的指称方式上所取得的共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显然不是因为双方具备了常识的观点,更不是因为具备了其它的观点而达致指称的共识;看来长辈们和小孩们是先有对谈,后有共识;因为孩子们不必预先掌握长辈们的一些观点,从而预先知道了单词句“兔子”只能够确认为个体或堆块的指称词,才得以通过交谈知道单词句指称着什么;说得更彻底一点,长辈们因为搁置了原来的常识观点,又没有拿出接替的观点,连他们也不必预先掌握某个特定观点,以限定单词句在起着指称作用时只能够继续在两种方式中选用一种;他们只须要依照既有的语言习惯让单词句“兔子”继续指称着个体,再适当地调动量词,便足以应付新科技兴起所触发的指称分化;孩子们通过交谈所确定下来的当不超出既有的语言习惯和调动量词的用意,并且在这些习惯和用意两个方面取得共识。
重视共识,有助于解释孩子们所知道的是否为长辈们的想法,认识“兔子”指称什么,也就认识长辈们使用这个单词句时所要表述的是什么;然而,认识长辈们所要表述的是什么,在蒯因看来,并不是语言学习的重要课题;因此,追求共识并不是语言学习的首要目标,翻译者的工作正好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在下一节里,讨论蒯因为什么相信翻译者不必追求共识,便可以掌握部落语言。
(六)理论、语言习惯与限定的指称
蒯因的翻译者全力找寻的是适当的翻译守则,让自己正确地把说话者的语句翻译出来,并且借助语言翻译来解释说话者的言行;寻找正确守则的主要方法就在于观察和推算,即观察说话者的言行和推算说话者在言行上的变化;有的时候为了搜罗更多与说话者有关的资料,让守则定得更准确,翻译者也会跟说话者交谈;是否因此与说话者达成共识,培养出相同的语言习惯和量词的用法,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掌握解释言行的假说,近乎无误地预测说话者的言行;为了坚持假说而不得不接受翻译守则,最多标记着追求正确预测所需要知道的一些情况。这样,根本谈不上是否有指称共识;这一点许多的语言使用者都认为是个疑问。
蒯因相信他没有给这个疑问所难倒;在他看来,翻译者的主要工作正如上面已经交代过的一样,就是要整理有关言行的资料,以便得出一些假说,再以此为根据拟定一些翻译守则,让后来者不必重新搜集资料,便可以在守则的指引下找到适当的假说,完满地解释说话者的言行;这样的工作是典型的科学工作,在翻译守则指引下找到的假说如果经得起科学验证就是典型的科学成果,翻译守则当与备受尊重的科学理论(例如解释言行的假说)享有同等的知识论地位;和其它的科学理论一样,它会碰上限定不足的情况,因为全面考虑说话者的言行的全部资料也不足以把翻译限定下来;虽然如此,翻译者所采用的方法到底享有崇高的知识论地位;他把说话者的语句翻译过来,让我们知道说话者所表述的东西,没有理由受到忽视;接受限定不足的情况,承认存在着别的守则,同样完满地解释说话者的言行,并没有带来什么损失。
不过,承认各个守则各言其是之后,千万不要这样推想:以为翻译者在限定不足的情况底下受困,永远不能够摆脱自己的守则,直接认识说话者实际上要表述些什么;以为说话者要表述些什么,当用那些语句,他心中有数,不必参照有关言行的解释;以为他所知道的虽然可以但不必通过翻译守则而表述出来。因为这样推想预设了像意义之类的东西为说话者所直接掌握,并且推想翻译者在熟悉说话者的语言之后也可能不必依据翻译守则而直接地拿到手;蒯因不相信存在着上述推想所预设的东西,他强调语句表述些什么东西,离开了翻译守则便确定不了;就算是从自己的口中说出来的语句,也要按照所采用的(同音翻译)守则来确定它所表述的是什么。
蒯因的这个观点还没有把他的语言观全盘展示出来,他除了否定在守则以外给确定下来的意义之外,他还否定了翻译者使用说话者的语言时所用上的语句总有一个解释符合说话者所认可的意义,为一个(特殊的)翻译守则所确定下来;蒯因提出翻译不可限定说,其中一个用意就是要借助不可限定的情况来说明没有这样的翻译守则;这个用意有的时候给另外的用意所掩盖了,连蒯因本人也没有察觉到;这里顺便一提,另外的用意就在于借助不可限定的情况说明不存在着任何的事实根据完全限定了翻译;因此,不存在着由限定的翻译所确定下来的意义。〔1 9〕至于利用不可限定说来说明没有上述特殊的翻译守则所依循的途径 是这样的:或许说话者亲自提出一些说法解释自己的言行,“gavagai ”所表述的就在形成解释的过程中给确定下来,所确定的就是说话者所要表述的意思;不过,翻译者所追求的并不是这个意思,所提出来的翻译守则也不是为了‘捕捉’这个意思;翻译者即使采用了说话者的假说来解释说话者的言行,相同的假说和相同的言行资料联合起来也限定不了“gavagai”该怎样翻译和该表述什么; 明白限定不了的情况就是明白这样的情况:说话者和翻译者都可以依据有关言行的资料制定假说,解释说话者的言行,并且根据不断改进的假说修改自己的翻译守则,务求守则能够配合自己(就说话者的行为所提出)的假说,帮助后来者更快地认识部落语言;由于这是科学活动,针对着有目共睹的研究对象(即部落言行),双方还可能进一步检讨彼此的假说,共同确定所提出来的假说是否正确;不过,双方却不能够脱离假说单独地为解释守则进行有意义的争论; 如果双方认为对方(的翻译守则)没有正确地掌握“gavagai”的意思,他们只能够重新检讨所搜集的资料是否准确和全面 ,再检讨各自的假说是否恰当;双方完全有可能承认对方所依据的资料既准确又全面,并且进一步承认对方的解释没有一处抵触部落言行;不过,就是没有同意对方所提出的翻译守则,不同意依据着对方的翻译守则来说明“gavagai”所表述的意思;既然“gavagai”没有翻译者一定要认同的意思,追问是否存在着一个翻译守则,以它来‘捕捉’说话者所认可的‘意思’,谋取共识,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讨论到这里,蒯因的意义观开始明朗化;他承认了翻译者没有必要追求说话者藉着母语所表述出来的意义,因为彼此不必有共同认可的句义;另外,翻译者也不必追求说话者为自己的言行所提出来的解释;因为即使有了共同承认的解释,也保证不了有共同认可的句义,更何况正确地翻译说话者的母语不靠共同认可的句义;那么,翻译者就不必知道说话者的句义便认识了后者的母语,这怎样说得通的呢?
让我们再以“gavagai”为例,说明这个问题蒯因可以怎样处理。 设想说话者在兔子掠过之前已经决定了“gavagai”指称兔子, 这样他就再没有理由认定“gavagai ”指称着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或者其它的什么东西;就算翻译者按照他的守则让“gavagai ”译作“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并且指称着这样的连结体时完满地解释说话者的言行,也没有得到最好的理由把说话者的指称按照翻译者自己的解释确定下来;谁知道说话者先前的决定,谁就得到最好的理由,把“gavagai ”译作“兔子”,并且让它指称兔子,怎样翻译“gavagai ”也就依照着说话者的意向而给限定了;然而,蒯因早就劝喻我们不要以为语言得到使用之前预先存在着意义或指称可供约定,不要以为“gavagai ”可以约定为指称着兔子;在他看来, 说话者不用别的单词句, 却经常用上“gavagai”来指称掠过眼前的某种东西也许是说话者所选择的用法; 不过,能够进一步确定这个用法指称着兔子却意味着说话者已经知道了掠过眼前的是一只“gavagai”所指称着的兔子, 知道了上述单词句指称着兔子实际上知道了说话者本人或者别的说话者在其他的时间和地点看到同类的东西掠过时便认定它为兔子,并以之为“gavagai ”的指称对象;认同这个指称(观点)完全因为说话者为自己以及其他说话者的言行求得完满解释时不得不承认“gavagai”指称着兔子; 说话者当然可以提出另外的完满解释,并可能因此而承认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为“gavagai”的指称对象; 看来说话者如果没有认可一些为自己的言行而准备好的解释,就无以确定“gavagai”的指称; 翻译者不可能撇开怎样解释说话者的言行这个问题,单独追求指称或意义。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先于解释的意义,为说话者和翻译者所掌握,这一点刚才已经讨论过了;另外一方面是由于双方不可能在没有认识对方怎样解释言行的情况下有意义地(以部落语言为媒介)争论部落语句在得到使用时表述了什么问题;这样的争论既不预先要求双方在解释言行上取得完全的共识,也不要求双方在争论平息后一定要在语句意义上达成完全的共识;例如说话者的母语是个汉语部落的语言,他说出了部落单词句“兔子”,也许他提出了条件反应说,并以此为据推想兔工场的活兔掠过促使自己说出了“兔子”,而“兔子”也因此而被视为指称着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假定翻译者也提出了条件反应说,据此确认繁殖出来的兔子掠过促使说话者说出上述的单词句,并且让它指称着繁殖而得的活兔,这表示了翻译者没有采用说话者原有的假说,因而用上了不同的解释;如果双方在其它许多的言行解释上取得共识,便有办法知道彼此提出不同的假说,解释部落人士为什么说出“兔子”,经过讨论之后知道两个解释分别谈论两种来源不同的活兔,翻译者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修改自己的解释,让它更恰当地说明说话者在新科技的环境里的言行;这个情况显示了意义没有的地位,只能追随着解释的修改而修改;而修改解释的用意主要在于更恰当地说明说话者的言行,不在于‘捕捉’说话者为“兔子”所确定的指称;翻译者和说话者一样,成为合格的汉语使用者不在于‘捕捉’说话者所确认的意义,而在于知道自己的解释被修改后,是否更恰当地说明汉语使用者的言行。
在另外的情况下,翻译者可能采用了说话者的假说,同意兔工场的活兔掠过促使说话者说出了“兔子”。不过,在翻译不可限定的情况底下,翻译者有可能认为“兔子”像以往一样继续指称兔子;也许他认为说话者没有刻意借用量词的新用法来标明“兔子”指称着兔工场的活兔时实际上是指称着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所以他依照新科技兴起以前的旧习惯,让“兔子”指称兔子,认为这样理解会更恰当地说明说话者的言行:如果翻译者因此拒绝修改自己的解释,不让“兔子”指称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这并非表示了翻译者认为说话者没有正确地理解“兔子”,更不是意味着他和说话者两人当中的一个错解是“兔子”;除非他们两人有共同的标准,否则两人当可各言其是;他们当然可以通过交谈,确定彼此的解释在那些地方出现了差异,同意怎样修改双方或者一方的解释;到了那个时候,便可以按照双方同意的解释来确定怎样去理解“兔子”才算正确;不过,追求解释言行方面的完全共识并非语言使用者的本份;他们的本分仅在于为说话者的言行寻求完满的解释,这是人类各项科学活动的一种;纵使人类只根据着一个科学标准来裁决所确立的解释是否完满或者是否须要修改,也不足以限定某个解释为汉语使用者的追求目标,让翻译者和说话者朝着这个目标进发,谋取共识;汉语使用者根本没有指定的共同解释,用于说明与“兔子”有关的言行;即使有共同的指引,也保证不了指称的共识;虽然如此,翻译者也不会因此而成不了及格的汉语使用者;求取正确的翻译或者正确地掌握说话者的母语,在蒯因看来,实际上就是为说话者的言行求取恰当的解释;怪不得他把语言学习者形容为科学理论的建造者。这样的语言学习者不用认识部落语言的句义,就可以掌握部落语言;原因在于没有句义可供掌握,所谓句义已经让翻译不可限定说所否定了。
不过,这不等于说充当一名理论的建造者,提出条件反应说,解释部落人士为什么说出“gavagai”,便完成了语言学习的一个环节, 学懂了怎样正确地使用“gavagai”去表述部落人士的想法。 解释言行到底有别于说明“gavagai”的指称; 如果掠过眼前的东西证实了不是兔子,翻译者便没有理由再坚持原来的言行解释,继续认定部落人士因为看到兔子掠过便说出了“gavagai”;不过, 翻译者仍然有机会找到理由,让自己坚持“gavagai”指称着兔子, 与说话者一起继续尊重原有的指称共识。因为有的时候,翻译者虽然知道了掠过的东西实际上不是兔子; 不过, 所得到的言行资料却清楚地显示了部落人士坚持以“ gavagai”指称着兔子,只要双方同意彼此之间的分歧涉及事实, 与指称无关,翻译者便有理由坚持原来的指称;如果让解释言行的理论与说明“gavagai”的指称的理论(即关乎单词句的性假设)混为一谈 ,便决定不了双方究竟在事实方面还是在指称方面产生了分歧。除非不得已,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接受混为一谈的主张;即使承认了翻译不可限定说,否定了学习语言在于‘捕捉’于理论之外的句义,也不等于主张既有的指称传统(语言的一种习惯用法)一定随着过去用于解释言行的理论受到摈弃而掉失;让翻译不可限定说只针对着句义,不针对语言的习惯用法,让语言不必依附于理论也有所表达,便不必附和意义上的整体主义;碰到翻译者和部落人士争论“gavagai”是否译作“兔子 ”时,也不必束手无策,决定不了所争论的究竟是事实的问题还是指称的问题;只要翻译者不受整体主义所困扰,总可以根据情况判断部落人士是否要维护原来的指称传统,也可以根据情况判断他们是否要放弃既有的(或者拒绝别人提出来的)言行解释;总而言之,就是要懂得分开处理语言(的用法)和理论(所提供的言行解释),才真正理解部落人士的语言习惯,才有能力使用他们的语言来说明他们的思想。
蒯因应当接受这个看法,因为他不是意义上的整体主义者,从来没有论证语言和理论分不开;他的主要看法都集中在翻译不可限定说,指出翻译者根据部落人士的言行、甚至根据他们为自己的言行而准备好的解释,也限定不了“gavagai”所指称的是兔子、 还是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虽然预先知道了部落人士以“gavagai”指称什么, 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部落人士在看见了掠过的东西时说出了“gavagai”; 而预先知道为什么部落人士说出“gavagai”也有助于说明部落人士以“gavagai”指称什么;不过,两者相互依存却不是指称限定不了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根本没有可限定的(指称词的)指称或(单词句的)意义要我们来限定,这就是翻译不可限定说的主旨;蒯因从来就不相信在没有解释为什么说出“gavagai”之前就有可预知的指称或意义, 而且不相信在得到解释之后也可得到限定的指称或意义;所以,他认为没有可预知或者可限定的指称或意义因为依存于解释部落言行的理论而无法予以确认;要当个意义上的整体主义者,至少要同意没有可预知的意义;蒯因虽然做到了这一点,却没有追随意义上的整体主义者进一步推断指称或者意义如果因为不存在于理论之外而成为不可预知的东西,它当存在于理论之内,为理论所限定;并且因为与理论相互依存而难分难解,在认识理论之前无以辨认;而蒯因从来就不承认理论限定了意义,当然不相信在理论得到认识之后意义便可以辨认出来;蒯因实际上否定了意义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从此学习的目光只盯在语言的习惯用法上;语言学习者所追寻的再不是由理论所限定的指称,而是语言习惯用法所限定的指称;这样,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按照部落语言的习惯用法便可以让“gavagai”指称着部落人士所要指称的东西呢? 让我们在下一节回答这个问题。
(七)假说、指称和想法
蒯因放弃了以意义为核心的语言学习理论之后,学习部落语言就不再被想像成为认识部落语句意义的过程;那么,部落小孩们要认识什么才掌握了长辈们的语言?要认识什么才懂得使用长辈们的语言正确地表述长辈们的想法呢?按照蒯因的设想,长辈们根据原来的言行解释制定“gavagai”的指称,让它指称着兔子(或者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 ;如果他同意长辈们即使放弃了原有的言行解释,“gavagai ”原有的习惯用法仍然得以保存,继续指称兔子(或者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那么,小孩们一定要认识的绝不是有关的言行解释,而是长辈们的语言习惯,才有可能使用“gavagai”正确地表述长辈们的想法。不过, 问题还要往后追朔,弄清楚究竟有没有可依据的东西,让长辈们的习惯用确地表述他们的想法;也就是要问:认为“兔子”在某个上文下理中、或者在得到某个用法时指称着长辈们所要指称的分立个体,究竟有什么依据?相信像克里普克(kripke)的意义怀疑论者( meaning sceptic)会特别关心这个问题,〔20〕因为他们深信没有任何可依据 的事物证实长辈们同意以“gavagai ”指称兔子(或者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的用法,也没有任何事物支持这个用确地表述了长辈们的想法;就算身为长辈,也没有什么可成为依据,确定自己的用法,以“gavagai”指称兔子(或者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 也没有什么可成为依据,确定这个用确地表述自己的想法。
如果长辈们担心自己的习惯用法是否恰当地标记了他们的想法;那么,以新科技生产活兔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应当关心这样的问题:量词得到了新的用法之后能够配合“gavagai ”的用确地标记着自己所想到的东西吗?即标记着新的科技环境里值得注意的个体结构吗?长辈们受到质疑的时候比较合理的做法似乎是马上反问这个新的用法是否有缺失而使它不能够配合“gavagai ”的用法恰当地标记着自己的想法;如果认为有缺失便要研究怎样补救;就算一时决定不了怎样补救才算理想,也尽快作出决定,把(不大合意的)标记的方法确定下来,让新科技所催生的成果(勉强地)得以表述出来;不过,怀疑主义者的问题不在于新的用法是否有缺失;而在于即使没有缺失,也没有任何事物——包括长辈们的意愿(或者临时的决定)——足以确定新的用法表述了长辈们的想法。蒯因的主要论说,并没有集中在意义上的怀疑主义,而是集中在不可限定说上;不过,关于后者的一些论述仍然值得借鉴,因为这些论述为解除怀疑主义的疑难提供了指引。
顺着卡纳普的想法,我们可以为部落语言拟定适合的语义规则,确定(单词句)“兔子”的句义;有了句义,便可以判断“兔子”是否正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蒯因早就否定了可预先规定的句义,当然不会以句义来说明语言的习惯用法为什么可以表述说话者的想法。按照他的,实地考察的语言学家制定翻译守则,让后进引用守则确定“兔子”的指称,这样做完全没有意思让守则取代语义规则;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意思让守则独行独断,为“兔子”确定指称,更没有打算以“兔子”的用法是否符合翻译守则来裁定它是否正确地表述了说话者的想法。
翻译者相信自己能够凭着“兔子”的翻译掌握了说话者的想法,受到意义怀疑主义者的质疑,后者所针对的可能是翻译者避免不了众多等效的守则,结果无以确定那一个守则揭示了部落人士所意欲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只要蒯因引用不可限定说,把情况交代清楚,便可以消除怀疑主义的疑虑;按照蒯因的想法,翻译者或者部落小孩要先提出假说,解释部落长辈们为什么说出“兔子”,才根据解释制定指称;尤其是处于极始翻译的境地,更要先拟定了怎样解释部落长辈们的言行,以及确定他们的想法,才制定翻译守则,让翻译出来的句子表述了长辈们的想法;假设翻译者认为部落长辈相信兔子掠过才说出“兔子”,这个解释意味着部落长辈有个想法,即相信兔子掠过;翻译者一旦同意了这个解释,就别无选择,以“兔子”表述兔子掠过的想法,并且让所制定的守则来体现这个选择的结果;那么,只要解释通过了检证,便可以确认“兔子”(汉语部落单词句)译作“兔子”(翻译者的单词句);在守则体现了解释所确定的想法之后,质疑守则的作用,不相信它能够帮助翻译者掌握部落长辈的想法,无形中也质疑了有关的解释,不相信它所确定的正是长辈的想法;由于蒯因所采用的解释正是科学家们所容许的解释;谁质疑这种解释,认为发生在部落长辈身上的任何事物都不足以证实有关的言行解释,谁的立场就和休谟的差不了多少,质疑一切的科学解释;当然,意义怀疑论者会强调他们所质疑的只限于意义方面的所有解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蒯因就不受意义怀疑论的胁迫,因为他早就放弃以意义为核心的语言学习理论了。
也许怀疑主义者所质疑的不再是意义,却指出部落长辈们没有任何的依据,确定“兔子”的习惯用法表述了他们的想法;那么,在蒯因看来,这个疑问实际上表示了翻译者、部落小孩们、以至部落长辈们本人即使选择了假说,据此认定长辈们相信兔子掠过才说出“兔子”,也不能够进一步确定这个解释意味着长辈们有一个想法,即兔子掠过;因此,各人无法凭着它来确定“兔子”的习惯用法是否反映了长辈们的想法;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不是所有的假说都引导翻译者或小孩们去认识部落长辈们指定的指称;有些假说用于解释长辈们为什么说出“兔子”时预设了兔子的存在,如果所预设的正好是“兔子”的指称对象;那么,有关的假说当可引导翻译者或小孩们去认识部落长辈们指定的指称,并进一步引导他们认识长辈们的想法;而有关的假说便称为相干的假说;怀疑主义者所担心的就是连长辈们也不知道那一个假说是相干的;结果不能够根据相干的假说确认“兔子”的指称,也就无法根据指称确定“兔子”表述了那些想法。
蒯因的不可限定说(即主张没有于言行解释的意义的学说)仍然是回应的基础;长辈们如果真的有了想法,例如相信兔子掠过,并且选择了“兔子”来表述这个想法,无论如何他要拟定一个假说来解释他的选择,然后根据解释制定“兔子”的指称对象为兔子,才保证得了他所选择的正好表述了他的想法;虽然他的解释限定不了他的指称取向;但是,他却不能够没有解释就用上“兔子”表述兔子掠过的想法;而且不能够没有相干的假说,否则,在必要时就没有适当的假说用于解释自己为什么以“兔子”来表述兔子掠过的意思,也没有适当的假说用于证明自己有上述的想法;长辈们说出“兔子”时之所以能够确定自己的确有兔子掠过的想法,完全在于他懂得靠着相干的假说来检定“兔子”是否适用于表述他的想法,而检定的标准就视乎他是否能够根据相干的假说把“兔子”的指称对象确定为兔子;在这种情况底下,质疑“兔子”是否表述了长辈们的想法,就等于质疑单词句的使用者(包括了长辈们)是否懂得识别有关的相干假说,以及是否懂得依靠相干的假说把“兔子”的指称对象找出来,从而检定单词句是否适用于表述兔子掠过的想法;这一系列的质疑实际上直接针对着单词句的使用者,怀疑他是否认识什么是兔子掠过的想法。这样的怀疑主义者质疑说话者的语言可用于表述他的想法。
蒯因所要回应的不是如此彻底地怀疑的怀疑主义者,他要反驳的是这样的意义怀疑主义者:他们坚持有一位部落人士,只知道自己有兔子掠过的想法,却不知道有什么相干的假说可以用于检定“兔子”或者其它的部落单词句的意义,凭着意义确定有关的单词句是否适用于表述他的想法;蒯因认为这样设想不妥当,原因在于想像中的部落人士既然保证不了那一个单词句表述了他的想法,也就无从确定他有想法,也因此确定不了他是否懂得辩论有关的假说和指称,藉此以检定“兔子”是否适用于表述他的想法;意义怀疑主义者所针对的部落人士实际上没有出现,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根本没有受到冲击。所谓意义怀疑主义,在蒯因的翻译者面前,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思辨。
(八)结 语
蒯因有关意义的学说除了要解答语句表述什么问题之外,还论证了个人所掌握的语言能力关乎言行解释的能力;后者有助于说明我们是怎样去维护语言互通思想的作用;按照他的进一步引伸,我们可以这样想:语言学习者在语言能力受到考验时,能够继承长辈们的做法,即追随长辈们挑选适当的假说,以假说为指引把“兔子”的指称对象找出来,再依据指称对象确认这个单词句适用于表述那一个想法,也就确定自己是否错用了单词句;长辈们也许会因应不同的的情况挑选不同的假说,让同一的单词句在不同的场合里表述不同的想法;后学如果要透过长辈们的语言充分掌握长辈们的想法,便要在许多不同的情况底下选对了当时的假说,这的确是复杂的事情,却没有难倒蒯因的翻译者;然而,先挑选假说,其次寻找单词句的指称对象,然后根据所得的指称检定单词句所表述的想法,很可能只是长辈们解决语言用法的一种习惯;小孩们有可能在旧假说被摈弃而新假说还没有形成的情况底下保持了长辈们既有的用法,这反映了部落人士可能还有别的习惯,不必依靠原有的假说便限定了单词句的指称,建造理论预言行可能不是常见的方式;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执着语言表述科学思想的一面,它还有表述其它各种思想的几个方面;有意修补蒯因的学说的人应该注意这个情况。
参考文献
[1] barrett,r.b.& gibson r.,eds.〔1990〕 persepctives onquine; blackwell(oxford,uk).
[2] carnap, r.〔1937〕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trans. by amethe eaton; k. p trench, trubner & co. (london,uk).
[3] _______〔1942〕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usa)
[4] _______〔1947 〕meaning and necessity: a study insemantics and modal logic; univ. of chicago press ( chicago,us a)
[5] chomsky,n.〔1969〕"quine's empirical assumptions" indavidson〔1969〕,pp.53—68.
[6] davidson, d.& hintikka, j., eds.〔1969 〕words andobjections:essays on the works of w. v. quine; d. reidelpublishing company (dordrecht,holland)
[7] hahn,l.w.& schilpp p.a.,eds,〔1986〕the philosophyof w.v.quin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 la salle,illinois,usa)
[8] kripke,s.〔1982〕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language; blackwell(oxford,uk)
[9] quine, w.v.〔1951〕"two dogmas of empirici",philosophical review 60, pp. 20—43. reprinted in quine〔1953〕,pp.20—46.
[10] _____〔1953〕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harper &row (new york,usa)
[11] _____〔1960〕word and object; the technology pressof the mit (cambridge, mass.usa)
[12] _____ 〔1969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essay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usa)
[13] _____〔1973〕the roots of reference; open court ( lle, illinois,usa)
[14] _____〔1990〕pursuit of truth;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cambridge, mass. usa)
[15] schilpp, p. a. ed.〔1963〕the philosophy of rudolfcarnap; open court (la salle, illinois, usa)
[16] wang, h〔1986〕beyond ytic philosophy: doingjustice to what we know;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usa)
注释:
〔1〕参考schilpp(1963)53—67页和900—905页;卡纳普在这两处简述了他的语言观,详细的论述见于carnap(1937)和carnap(1947)。
〔2〕即carnap(1942)。
〔3〕蒯因写文章直接冲击卡纳普的语言观最少有四篇, 它们分别是quine(1936,1951,1956,和1960)。参考gibbson(1990)xiv —xv页,wang(1986)252页。
〔4〕参考quine(1951)20—37页。
〔5〕参考quine(1951)37—42页。
〔6〕例如j.katz等语义学上的柏拉图主义者(platonists)。
〔7〕即quine(1960)。
〔8〕参考quine(1960)第ix页,(1969)第26页,以及(1960)第81页。
〔9〕实地考察的语言学家第一次接触从没有听说过或记载过的部落语言,唯有依据现场的部落言行拟定部落语句的翻译;没有提出假说解释部落言行,就拟定不了翻译,这是蒯因所指的极始翻译(radicaltranslation)的情况;蒯因喜欢谈论这个情况。因为他相信设想这个情况有助于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学习语言的困难。(参考quine 1960,26—30页。)
〔10〕蒯因说:“语句的意义根据支持和否定它的观察而定;由于学习语言在于学习它的语句,因此,要认识那些观察成为支持和否定这些语句的证据;观察和理论之间的凭据关系和语义关系是重叠的。”(译自quine 1973,第38页。)这说明他同意了建立理论解释部落人士为什么说出“gavagai”和建立翻译守则说明“gavagai”指称兔子都以相同的证据为基础。
〔11〕蒯因说:“为科学而设的证据不管怎样一定是官感的证据,……而灌输言词意义(的知识)最终以官感证据为依归……”(译自quine 1969,第75页。)这说明了他心目中的科学家和语言学习者所依循的正是相同的官感证据。
〔12〕参考quine(1960)90—95页,105—114页。参考quine(1973)52—59页。
〔13〕蒯因的翻译者(即外族的受话者)很可能根据他的翻译守则让“gavagai”指称兔子, 而部落人士却可能指称着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造成指称分歧,有的时候无关于两人所得的证据,却涉及两人是否同意赋予掠过的东西相同的本体论结构;后者所得的证据如果支持他以掠过眼前的东西为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并且支持他的假定,以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驱使族人说出了“gavagai”;那么, 同时同地所出现的证据也支持前者的假说,以兔子触动了条件反应;如果后者有理由根据自己的解释来确定“gavagai ”指称着兔子各个部分的连结体,那么,前者也有理由根据兔子触动条件反应的假说,把后者的“gavagai”理解为指称着兔子;因此,即使翻译者正确地翻译了“gavagai”,却无法知道部落人士想的是什么东西,这的确恼人。
〔14〕参考quine(1973)45—49页。
〔15〕参考quine(1990)42—43页。参考gibbson(1990)3—4页。
〔16〕参考quine(1969)6—16页。quine(1974 )第三部分详细地讨论了指称个体所要考虑的情况。
〔17〕参考quine(1973)41—45页。
〔18〕按照蒯因的,语言学习在于掌握翻译同义句(或词),所掌握的与理论物理学同样没有被资料(或证据)所充分限定(davidson 1969,第302页),因此小孩和科学家分别选定的守则和理论都没有被充分限定;不过,他们所选定的都要符合节约原则(quine 1973,134—137页)。相似之处甚为明显。
〔19〕参考davidson(1969),第303页。参考hahn(1986)155—157页。
〔20〕有关意义怀疑主义,请参考kripke(1982)7—54页。
本文地址:www.myenblog.com/a/28607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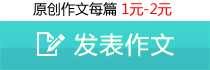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