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痴迷为话题
在我的记忆之中已没有这方土地最初的模样,想必是静谧安详,在湖中看得到自己的灵魂的。老人痴迷的,是那样的纯净。我疑惑的是,需要如何的爱恋,才能继续痴迷于如今它的不堪。
——题记
时下天气已渐显了秋日特有的肃杀之气,尤其是在落日挣扎、天色欲黑未黑的黄昏时分。我踏在这条记忆中是凄清的路上赶到奶奶家吃饭——在很小的时候搬家后一同吃饭成了很稀有的事。
任谁都会惊异:这条并不宽阔的水泥路两边停驻了各色轿车,许多提着渔具的男子和穿着艳丽的女子从车中走出来。湖面倒是还闪着点点光亮,前些时候听父母聊天时说起,这个村中的湖被开发为远近闻名的垂钓点。我不由感叹发展的速度。
远远地看到一位和这一景象极不相称的、穿着藏青色布衣的老伯伯迎面走来,等近些才发现是个熟人。但我不知他姓什么,农村中把老人叫作“阿爹”,因为从小被这么教,也就自然不知姓名了。我唤了他一声,他微微抬起头,眯了眯眼,然后恍然大悟似的,“你来奶奶家吃饭?多回来走走挺好的。”我问他这时候要去哪儿,他朝着湖面上一座木屋努努嘴,眼神中有着深深的依恋。我并不明白,也无暇多问便同他告别,看他的背影消失于转角。奇怪这和周围人物不相容的背影,竟同那一片湖面毫无嫌隙地融合。
饭间提起老伯伯,才得知由于土地征用的缘故他原本的住所已没有了,分到了镇上的房子,但他不愿去。正好垂钓点需要一个人象征性地看守,他就跑去同领导要求,得到了这份几乎没有报酬的“工作”。村里的人都说他不开窍,他却说,“在这里一辈子了,离不了它了。”
天色已完全黑下来了,夜空却没有一颗星星,显得愈发黯淡。屋中的人还在吃喝,我独自到湖边散步。湖面与失去光泽的夜空却是极大的对比:许多人走在湖面新架设的木质小道上,笑啊闹啊还有轻浮的玩笑话;观察钓鱼用的灯光刺眼极了,怕是惊扰了这一湖的好梦。我在木屋旁遇到老伯伯,便停下来听他絮叨。
“他们许多人每天都来,常常待上一整天。一到周末人就更多了,就像今天。”老伯伯略显无奈,深深地凝视湖面。继而转过头来,说:“记得你三四岁时就爱坐在清清的河埠头,大声喊每一个路过的老人‘阿爹’,而我们一叫你‘洋娃娃’,你就生气假装不理人。”而后稍垂下头,像在思忖着更多的记忆。
“是这样啊,我都不记得了。”我抱歉地对他说。
说话间不远处传来了欢呼声,像是有鱼上钩了,但欢呼很快停止。“他们啊,钓起小的鱼就不要,又放回湖里。可是被扎过的鱼是要死的,我就每天划个船把湖面上的鱼捞起来,喂附近的野猫。”他叹了口气,又望向湖面,目光落在不知名的远处。在他的提醒下,不知是心理缘故还是怎么的,似真有一股鱼腥味缠绕在四周,缠绕在他们放肆的笑声里,也缠绕在老伯伯凝望的视线里。
我要走的时候,钓鱼的人们也正要离开。我看着老伯伯踏着笨拙的步子,走过每一寸被外人踏过的土地。缓缓弯下僵硬了的腰,捡起人们留下的塑料袋、泡沫饭盒。弯下腰,又撑起身体,又在另一个地方弯下腰,却还是捡不起被留下的刺鼻的汽油味和恶心的鱼腥味。只有湖面恢复寂静,默不作声地目睹老人对它的守候。
夜色之中还有老人永恒地陪伴着那里的今生与来世。
本文地址:www.myenblog.com/a/9645.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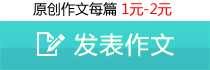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