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灵魂加密
人类作为独一无二的生命体,拥有会因他人的苦难而心生悲悯的灵魂,这是我们之所以称其为我们的依据,也是一道人工智能穷尽算法也无法解答的最终程序。然而,当某一天你发现大街上游荡着一张张相同的面无表情的脸,你该为此悲哀,因为人类文明的末日到了。
现代社会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支撑着人类的现实生存,它就像一台精密、庞大的机器,身在其中,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然而,在我们如同人工智能日复一日完成自己被预设的工作程序之余,又有多少人注意到了“小悦悦事件”等令人瞠目结舌的社会悲剧?这些社会悲剧就像一架天平,警醒我们不时称量一下人类的价值选择,天平一端放的是浓烟笼罩的工厂,另一端则是我们永恒的道德灵魂。过分夸大物质产出的流水线社会恰恰忽视了远更为复杂的精神活动——人的思想并非流水线。因此,我们时常难以分清天平两端孰轻孰重,正如我们时常难以确定自己的坐标,时常在白天的人山人海和夜晚的灯红酒绿间像个皮球来回滚动,我们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个体,我们的价值选择一日日犹疑,价值边界日益模糊。若我们如此般继续下去,我们终将去无方向,失掉灵魂,沦为一台台冰冷的计算机。
现代文学大师卡夫卡就描绘了人类被物化的情景。《变形记》中主人公变异成臭虫,何其荒诞!然而,荒诞背后的荒诞却是主人公的一家人竟漠不关心,自始至终毫无情感波澜,甚至从没想过怎么将自己的亲人变回人身,而是机械地给其喂食、弃置在房间深处。可以说,格里高尔一家人在社会重压之下丧失价值和同情的怪异行为模式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就像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臭虫并且失去周围人的怜悯,孤独死去,当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也被“异化”之后,我们就会支离破碎,随时可能会被社会“孤立”,这种孤立更多的是精神层面冷漠的疏离。我们看似身处紧密而复杂的社会大网中,但如同计算机,哪一天电源一关,一切便会溃散,人类的灵魂也终被破译。
对此,梭罗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超验主义的救赎。他远离迷宫般的工业城市,只身来到瓦尔登湖畔建造小木屋,饮食起居,散布种豆。这个过程对后工业时代朝人工智能时代大步向前的我们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也有幸像梭罗注视瓦尔登湖一样注视我们的心湖,我们会看见自己的倒影,看见人类特有的充满感情的眼睛,由此我们会对周围的事物心生同情,重新确定自己的价值,加重我们的灵魂。梭罗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始关心自然生长,关心瓦尔登湖的缩减,换言之,我们是在关心周遭事物的苦难和兴衰,我们在关心他人的不幸并散播同情、传递爱。所以说,我们只有拨开芜杂的物质屏障,才能真正寻找到自己失落的灵魂并为其加密。
诚如卡夫卡所言,“笼子在寻找一只鸟”。我们生来有翼,懂得贴近世界,但现代社会的笼子多多少少像陶渊明笔下的“樊笼”将我们套住,让原本造物的我们反过来被物统治,变得失去价值观和同情心,而后我们可能果真会如同臭虫般用六条小细腿支撑自己沉重的躯壳,最终,等待我们的只能是臭虫临死前冷漠地注视的这个世界,这个被异化为超级计算器的世界。
我们应像梭罗,努力挣脱“卡夫卡的笼子”,以一种战斗姿态做着抗争,而非听任物质的异化。我们应通过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和周围的人们心生同情,从而重新审视自我,唤回物质屏障背后落满灰尘的灵魂,并为这道最高程序加密,直至人工智能永无破译的可能。它将被写入只属于人类的永恒的生命线索中。否则,等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末日真正来临的那一天,你从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臭虫,而你的父母面无表情地说:抱歉,无法识别这种生物。
本文地址:www.myenblog.com/a/14016.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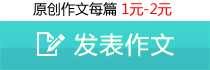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