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柴膜
搬家时,整理一个书柜,手指在一叠不知道多少年前的报纸后面碰到了一个白色泛黄的塑料方盒,上面纵横两条红色的布带绑得严严的。我很好奇是什么,想抽出来竟然挺费力,盒底已经似乎粘在抽屉的木板上了,稍稍用点力抠开,“吧啦”一声响。
那是用细腻的蝴蝶结绑起来的布带,很明显是父亲的手法,迫不及待解开,灰尘便在空气里蔓延开来。轻轻揭开方盒的盖子,一股久违的特有的陈味告诉我,里面满是厚厚几层芦柴膜。
我小的时候不比现在的孩子,功课也没那么多,课业也没那么繁重,每天在学校完成了一些书本知识便可以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龄的伙伴们几乎都爱去操场扔扔篮球,亦或跑到小店里买几包“唐僧肉”、“老虎肉”躲在角落美美地尝,然而我倒不大爱走动,除了在教室拉着几个玩伴一起讲脑袋里杜撰出来的各种神怪武功之外,最大的乐趣便是去办公室跟着韦总学横笛了。
小心翼翼地捏起一片柴膜,轻轻搓掉内壁细细密密毛绒绒的絮状物。剪一块试试吧,看看还能不能吹出童年的声音来。
韦总是位三十多岁的男老师,因为在小学里担任财务总监,而且深得孩子们的喜爱,因此大家都亲切地喊他韦总,而我之喜爱他的原因也就是他端平横笛吹出了那一曲曲悠扬悦耳的曲子了。每每看着他仔细地贴好笛膜,找办公室一处稍宽敞的地儿站好,伴着脚下轻轻敲打的节奏,任凭笛声从他一张一翕的指间飘出,那都是一次次极细腻的享受。倘至笛声高亢处,韦总俨然一名虔诚的宣誓者,左眼的眉头轻挑上去,坚定而又不失柔和的眼神望着窗外的远方,无限沉醉。那样伟岸的画面一直定格在脑海里,仿佛那就是童年记忆中的英雄。
四下无人的时候,我也偶尔端起横笛,模仿韦总的样子贴好贴膜,左脚轻轻打着拍子,微昂起头望着远方,眉头轻挑,纵然笛子不比那么精致,笛膜也只是找块透明胶替代,节奏也没那种韵味,笛声更比不上韦总的动听,然而在那么一个时刻,仿佛我自己也沉醉了,也伟岸了,仿佛世界都是我的了。这种孩子纯粹的境界,现在想来是多么有趣而且可爱。
第一次开口跟父母要零钱,不为一袋糖果一只陀螺,就是那么几片笛膜,是大毛竹里的提取品,贴在笛子上声音很清脆,花五毛钱买上一小袋,够用几个星期的。然而五毛钱于那时的父母来说也不无难处,一次放学回到家,见满屋子水泥方砖铺成的地上都是芦苇杆儿,芦苇叶子撒得东一片西一片,父亲、母亲、外公都坐着剥,身上、头发上全是干枯的苇絮,旁边地上一个白色塑料方盒里全是剪得很齐整的一段段芦柴膜。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心里的乐劲儿,书包一甩就跟他们一起剥开了,一家人围着一捆芦苇杆儿,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日子虽然贫寒,却依旧觉得幸福。如今长大了,随处可买到比芦柴膜高档数十倍的笛膜,然而那些包装精致华丽的玩意儿,在我总觉得少了点味道。
繁星满天的夏夜,父亲会搬两张木椅在门前,我站在木椅上吹横笛,他在一旁坐着听,为我摇扇子,我会吹很多曲子:《喜洋洋》《新白娘子传奇》《翻身道情》……没有谱子,都是自己摸索,幸而也渐渐能吹出点模样。邻居跟母亲说晚上听不着我的笛声就很难睡着觉,我于是每晚愈加卖力地吹奏,似乎那就是一场场音乐会,那些没有面对面的人们都是我的听众,而我总在用旋律触摸他们心底最真实的地方。这样表演着,技艺也渐渐纯熟,我想横笛给那无数个夏夜带来的除了欢乐,大概还有孩子天真的自豪感吧。然而究竟邻居有没有听我的笛声,母亲究竟有没有听他们说过那些话,我已经无从知晓了,只是那时候的一头热劲儿,到今天似乎也无从寻觅。
一根细细小小的横笛,一枚方方窄窄的芦柴膜,在点点繁星的夏夜,演奏着少时童真的我心中一曲曲盛大空前的音乐会,那许是农家夏日晚上最快乐的童年了。
我取出箱子内壁的横笛,把剪开的一小块芦柴膜贴上去,韦总说过,笛膜要贴得皱皱的,吹出来的声音才有震动感,才清脆。轻轻吐一口气,悠扬的笛声在指间萦绕开来,芦柴膜震荡着的时光在心底回荡,但那年少时满含情愫的说不出的笛声,却再也找不回了。
本文地址:www.myenblog.com/a/1120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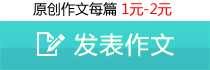


猜你喜欢: